芙蓉·小说丨姬中宪:两公里以内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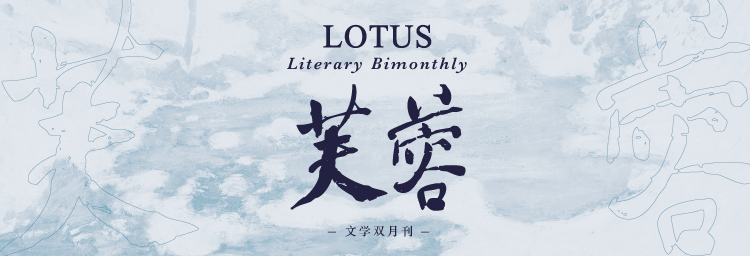

两公里以内的玫瑰(短篇小说)
文/姬中宪
微信上加了一个“附近的人”,头像是手绘的女孩侧面,露着肩,引人遐想。该怎样和她打招呼?这也许是我们一生故事的开始呢,我需要一句好莱坞爱情片中的对白,既浪漫新奇,又不至于吓跑她……我在对话框中反复编辑我们的第一句话,一不小心,发了一个“1”。
我正想撤回这条消息时,她的回复已经到了。她回了一个“2”。
作为一名聊天高手,这可难不倒我,我回了一个“3”。
她心领神会,或者也真是无聊,回了一个“4”。
我们相隔2000米,我们的心如此贴近。其后几天,我一直活在一种不规则的计时中,这计时遥遥无尽头,我是其中奇数的一方。
有时我要等很久才等到她的回复,她大概正忙,正与人交谈,正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总能等到她的回复。那是一个明确的偶数,它毫不意外,我却仍然期待它,好像只有等到那个数字,我体内那架生物钟的秒针才咯噔一声,往前走一下似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与我如此高度吻合,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倍感温暖。我们选择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将度过漫长的一生。
截止到发稿,我和她,已经聊到了54351。
她是画出来的。我每隔几天就忘记她一次。我从她这里学到的最新的一个词是“眉粉”,一种用来勾画眉形、塑造骨感眉的粉末,方法是用刷子蘸一些,从眉头到眉梢顺势扫下去。眉头到眉梢的长度,以嘴角到两个眼角的延长线为基准,长了或短了都会感觉怪怪的,因此她画眉时总是不苟言笑,生怕嘴角一动,影响了眉毛的长度。
眉粉据说有7000多种款式,哪怕她每天换一种,也可以保证二十年不重样。市面上还流传一些违禁粉,它们不在这7000多种之列,通常包在锡纸或香烟盒中,黑市上交易。女人们偶尔得到几克,立刻就近躲进一间黑屋里,将它三或五等分,然后留出今天这一份,一颗颗扫入眉中。再出来时,整个人都更新了,像刚刚遭遇了爱情,整个人重生了一次似的。
“女人的化妆业已经精细到快要为每一个毛孔发明一套产业链了!”我有一次对她感慨。
“你怎么不说你们这些男人的颜控已经深入到快要为每一个毛孔建立一套审美观了!”她回应我。
她一转身就消失。她花在后背上的修饰力度远低于正面。她只在某个特定角度下才是她。这当然是我——一个资深脸盲症患者的偏见。她消失了,我看到更多人向我走来。
她每隔几十秒就摸一下辫子,以确认它还在不在。
为了掩盖这动机,她准备了很多套摸辫子的动作,来表明她每一次都有一个实用的目的,比如有时她把马尾辫等分成左右两束,然后一手握住一束,用掰开一个核桃或打开飞机救生舱门的力度,死命往两边扯;有时她选出最长的一根手指插进头发,像吃意面一样将发梢一圈圈缠绕 ;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快速抚弄一下,好像感觉到一只苍蝇趴在头发上,或是一小撮头发翘起来了,或者只是觉得头发是一个需要时时安抚一下的弱者,因此不管多么忙碌,总要匀出一点时间,照顾一下它的心情。
这都是假象。她并未将头发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哪怕衍生物。毕竟很少有人时时焦虑自己的耳垂、大脚趾或胆汁是不是还在身上。她对头发的关照,源自对贵重随身物品的安全性的担忧,她每一次把手伸向脑后都带着一种预期——辫子丢了,刚刚还在的,突然就丢了。
辫子于她,是一种股票式的存在,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动态的、充满风险的拥有。“就像你洗完澡后发现刚刚脱落在浴缸边上的婚戒不见了,然后过了不到两个月,你莫名其妙地离婚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烦恼。
而我认为事实比她说的还严重些,因为那一根马尾辫很可能根本不是她本人的,而是某位贵人寄放在她后脑勺上的,她因此更加忧心它的安保,万一丢了,于钱于面子,怕是都赔付不起。
我与她是互为病人的关系。此刻她是我的病人。作为一名尽职的治疗者,总要给病人一些解释,最好是超出病人原有认知的解释,我于是给出了上述解释。“那你呢?你也经常这样担心你的头发吗?”病人反问医生。
“我……”我明显没准备好,“我当然也会有,比如每天早晨我一醒过来就要确认一下头发还在不在,但这可能源自男人对秃顶的古老的担忧,以及对假发这种可能性的根深蒂固的排斥,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此刻我是她的病人,她从我的身体上稍稍离开一些,残酷地笑了,好像要宣布我的不治。
“最重要的是,”我镇定下来,“我的头发是我自己的,而你的更像是身外之物。”
我和她的认识纯属意外,她在一家创意公司上班,那公司表面上高度依赖灵感、脑洞与天马行空,其实正相反。“我要做的仅仅是动手,而不是动脑,”她说,“只要我的手足够熟练、听话,保持随时操作的状态,我就可以完全胜任我的工作,所以……”
所以她现在很苦恼,每隔几十秒就要摸一下辫子的强迫症已严重影响到她的创意工作,“事情根本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她一边摸辫子一边说,“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当你思路中断时,摸一下头发,或者点上一根烟,立刻计上心头——不是这样的,我和他们不同,我只是创意流水线上的一个蓝领工人,我的手被机器全天候地征用了,摸一下辫子,可能就是一场生产事故。我也想过干脆把辫子剪掉,可是剪掉又能怎样?你没发现很多光头也喜欢时不时摸一下光头吗?还有那些大肚子的人,而头发的尴尬就在于它总是和你躲猫猫……”
“等等,”我打断她,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认识这么久才问这个问题让她很不适,但她还是告诉了我。也许正因为我问得突然,她来不及躲闪,出于本能回答了我。那是一个颇值得骄傲的名字,而且她一说我就知道是哪几个字。这名字赋予她一种神圣感。她随即正一正脸色,拿出一张名片给我,好像一段关系终结,我们要重新开始认识一样。她的名片四角尖锐,我被它划了一下。
“不对,”我像核对证件一样把她和她的名片放在一起审视,“这不是你,你不叫这个名字。”
走夜路,路遇一只手套,丢在地上,饱满有形,好像还有一只无形的手戴着;切面漆黑、整齐,像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砍下来。走几步,又遇到一只,然后又一只,然后是一堆,个个饱满有形。
那晚剩下的路,我提心吊胆,怕一转弯,遇到一群断手的人。
“我很好奇,你给我的备注名是什么?”
她是那种只要遇到一个反光的物体就不放过一次照镜子机会的女人。有时她在赴约迟到的途中经过一个卫生间时,也要下意识地停一下,对着大理石墙面——那墙面刚被阿姨擦洗得光可鉴人——整理一下头发,或是侧转身,扭头,收腹,就着墙上的暗影检查自己的臀部是否还像昨天下午一样上翘。
她希望时刻看到自己,最好是360度无死角的全息式影像。化妆镜这种小物件简直太坐井观天了,她恨不能每天躺进一台CT美颜机中,做那种俗称“切黄瓜”的切片式扫描,并像私家侦探那样将扫描报告图贴满整个房间。
即使如此,她还是因为无法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深感苦恼。她的夙愿常在梦中闪现——她钻进别人的身体里,从别人眼睛里看自己一眼,哪怕就一秒,此生不再遗憾。
此刻她坐在我对面,正在热烈地徒手吃一份泰式咖喱虾,然而看到我手机屏幕上出现了我和她的聊天对话框后,她立刻停下来,伸出唯一干净的一根小指,把我的手机屏幕扳过来:“我很好奇哎,你给我的备注名是什么?”
我给她看了,她略有些失望:“就是我的全名啊,好官方哦——咦?在描述一栏备注的是我原来的网名哎,好可爱,我自己手机上都看不到了,你说我要不要改回来?”
她后来干脆抢过我的手机,用一只手掌虚托着,用另一只手的小指快速翻到她的微信朋友圈,找到她最近的一张自拍,点个赞。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像操作自己的手机一样熟练。
“你改不回去了。”我拿纸巾擦掉手机屏幕上的咖喱汁,冷冷地宣布。我与她的爱情始终无法超过一顿饭的时间,我们只好一次次从饭桌上退下(如同重启,或退出登录),回到各自的手机前。
我在泰国餐馆外面坐等叫号时,遇到一件怪事。
起初我以为她们对我身后的LED招牌感兴趣,或者只是为了拍下餐馆的名字,发给正赶来赴约的男友(如今人们只要能用一张图搞懂的事,就绝不浪费一个字)。慢慢地我发现她们眼光异样,且动作过于一致——她们的拍摄有一种半公开式的遮掩。我终于醒悟:她们在拍我。
我心情复杂,身体就有些不自在。毕竟我也不是什么网红,不便于站起来冲上去,向她们索要手机,或是大声主张肖像权,万一人家出示手机,屏幕上并没有我,或者只是不小心拍到我一只脚和半张打哈欠的脸,那丢人的还不是我?
我直一直腰,表情庄重些,就像拍证件照时摄影师要求的那样。她们看出来我知道了,索性公开起来,一面拍,一面羞涩地和身边人小声议论。人越来越多,有等叫号的,也有路人,都在拍我。我站起来,走到叫号台,背对着她们,亮出我的号码:“请问,什么时候排到我?”
“哦!先生您好,您前面还有五桌。”迎宾小哥明显比刚才客气了很多,然而语气里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好像不这样才是对我的冒犯。我继续面朝着他,没有说话,只是为了避开身后的摄像头与议论,小哥却误解了,以为我在对他施压,他嗫嚅道:“要不我进去帮您看一下。”他逃掉了,把叫号台留给我。
我翻看台上的一本菜谱,坚决不回头。
“先生您好。”小哥回来了,站在门里面低声招呼我,同时躬身摊手,要借我一步说话的样子。我赶紧进去,经过餐馆玻璃门时,我看到身后一片相机闪动。“是这样的,有一桌客人临时取消了预约……”
有些餐馆就是这样的,你只要逼一逼,就能逼退一桌预约的客人。我坐进包厢,给她发消息 :进门左转到底再右转,第二个过道再左转,然后右手边第三个包厢。
20分钟过去了,她还没找到我。其间她至少三次从包厢门前走过。我的手机快没电了,那里储存着我与她的所有秘密,一旦没了电,我们可能会像两个断电的机器人那样定在原处。而此时,她还在消耗着我为数不多的电量——手机上,她的消息一条比一条气急败坏:“你到底在哪里?”“这什么鬼地方?再找不到我走了!”
我看她一次次从门前走过,感觉这样的捉迷藏游戏如果一直进行下去,也未尝不可,我们并非一定需要一次实体性的会面。然而有一次她明确看到我了,可还是走过去,不是赌气甩下我而去的那种走法,而是纯粹陌路人之间的那种走过。我突然有所醒悟。我拉起包厢的门,打开手机摄像,调到自拍模式。
屏幕上显示的是另一个人的脸——那是一个我最近很关注的,经常在屏幕上出现的,全国人民都认识的脸,恕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然而千真万确,此刻他的脸长在了我的头上,我惊讶地张大嘴时,那人也张大了嘴,我瞪眼时那人也瞪眼,我从他的五官中看出了我的神情。
我的最后一点电就是这样被吓光的。
之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乏味:她找到了我,她一进包厢就踢掉高跟鞋,像牧羊姑娘挥舞皮鞭一样挥舞起她的包包,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怪我不出去迎接她,直到有人敲响包厢的门。
“先生您要的充电器……”刚才那个小哥探头进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错包间了。”
“你没走错,”我从他手里夺过充电器,“我正好没电了。”
她有一整套拍照用的动作,正面、左侧、右侧、背面,每次都从四个角度各拍一张。给她拍照时,总感觉像给犯罪疑犯人拍照。
手也有常用姿势:胸前抱爪,双手绽开捧脸,或是背身单臂举起一个“二”;头发也有讲究,通常把发梢从颈间往前拨出一些,好遮出一个尖下巴;脚一前一后,摆出将走未走的样子。
有时她要求拍半身,实则拍到长裙的裙角,不露脚,说这样“显高”。我第一次理解错了,以为半身是到腰那里,结果她拍完过来检查,说拍错了,要求重拍。于是再站回去,极耐心地摆好姿势,正面、左侧、右侧、背面,再拍一遍。
所有这些照片里,她一律嘴微张,望向右侧45度,翻出大半个眼白,扮一副无知相。
虽然热,但她一直把外套拿在手里,我几次劝她放回去,她都不肯,起初我以为她害怕傍晚降温,后来才明白那衣服是拍照用的:比如把衣服系在腰里,或是披上,或是披上但是露出两肩,一件衣服穿出几件衣服的样子。
中场补妆时,她终于肯把外套放回包里,却又换出一件披风——她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物尽其用了——于是整个下半场更加花样百出。
我注意到她不喝水。我是那种一出门就要带水杯,遇到饮水机就要灌满的人,尤其是这样的热天,走几步就要口渴,她却一个下午都不喝水。只有几次,她背对我坐下,仰起头,往眼睛里滴几滴滴液。滴完就长出一口气,活动一下肩颈,浑身都很舒坦的样子。那滴液呈明黄色,略黏稠,像机油。
她对这人造公园里的每一处道具都十分买账,总要站在那道具的前或侧前方,将上述动作重复一遍,比如一辆水泥做的红色法拉利、铁皮包裹成的双心、螺旋上升巧妙收尾如一坨巨型大便的抽象装置、留着大胡子不知姓名的外国科学家或哲学家半身像……风格十分混搭。其中她最爱一匹马,由PV板制成,固定在地面上,体态矫健。这一次她对我的拍照角度要求极苛刻,即使她已在马前摆好姿势,仍不忘对我喊话,遥控我往左或右移动几厘米,好像我是一架行走的声控自拍杆。她后来向我解释,因为那马是平面的,角度稍一偏,就会露出PV板丑陋的包边,如同看三维画,能且只能站在她指定的那个点上,那马才不至于露出马脚,才有了血肉,好像随时会腾空而去一样。
那是一匹标准的二维马。
她有一顶宽边帽子,一戴上就再不肯摘。帽檐四周等宽,像在身体四周建起一圈护栏,加上卷发刘海又娇贵,口红又容易沾——她因此成为一个不能碰的女人,一碰整个人就花了。我给她拍了一下午照片,她最后也至多允许我从后面抱抱她,免得弄坏了她的正面。
她是我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约见的第七个机器人。说实话,七个里面,她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
她有一对年久失修的眉,还有方块形冰凉的牙。她从头到尾都不让我看到她,我只是凭触觉来想象她。“你是谁?”我问她,她不回答。
“我在你的附近。”她后来没头没尾地说。
她说得没错,她是又一个“附近的人”,系统显示,她在我2000米以内。
2000米以内,又生着这种眉与牙的女人,应该是有限的。我尤其记得她牙齿的形状与触感——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据说尸检时可以用牙齿鉴定死者身份,考古学家则根据一颗牙齿的化石还原出古人的音容笑貌、生活起居。非专业人士想记住一颗牙当然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窍门,我的窍门是:以牙记牙——我将那形状与触感储存在我的口腔内、唇齿间。
有这样一对关键词,不愁检索不到她。
我首先推理出她的走姿——我从未见过她走路,但福尔摩斯也是这样断案的——她右腿略短,右脚脚前掌外翻,走路微跛,这从她右侧牙齿的咬合度上可以明显推断出来,然而欺骗性也在这里:她的跛是肉眼看不出的,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只有精密仪器才能勘测出的微跛,所以你如果带着寻找一个瘸子的念头满大街找她,就必然要跑偏。我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比如,她走路时总是上身先探出去,两腿再跟上,好像她的身体内部没商量好,上半身想走而下半身不想走似的。这种自我协商以及轻微的胁迫感贯穿她走路的全过程。我从此开始留意周围人的走姿。
同样是上身前倾,她就不同。她——此刻从我身旁走过的一个女人——两臂左右摆得厉害,像行走的钟摆。她走在冷风里,头往前俯冲,随时要跑起来钻进风里的样子。这样的姿势如果放到男人身上,就是一出很好的喜剧表演。我跟着她走出几条街,一度觉得我要得手了,然而在红绿灯前她猛回头,吓到了我。
她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经理,而我还欠着去年第四季度的物业费没交。
再比如她:她走路时甩胯,右手前摆时甩左胯,左手前摆时甩右胯,方式是把臀部快速抖动一下,立即收回,以预备下一次反方向的抖动。这大概源于某种松松垮垮的偷懒式生活观,也足以吸引后方的异性。
再比如他(我也开始关注男人):他走路时脚尖点地,身体起伏,手臂摆得欢快,好像刚做完一件得意的事,但是他一不留神走错了自动扶梯(原本想上楼结果走到朝下的扶梯口),为了紧急制动,他整个身体都扭曲了,险些摔倒在扶梯上。他后来在扶梯旁稳了一会儿,眼神散乱,似乎他半生经验都被颠覆了。
还有他,走路时也爱甩胳膊,不同之处在于右臂甩的幅度更大些。如果他是一艘船,这样划桨可能会原地打转,但作为一个人,他有能力笔直朝前走。他内心有一股制衡的力量,他未来可能毁于动脉硬化。
我发现人完全不必以男女分,或以别的标签分,人完全可以用走路的姿势分。这可能更接近本质一些,以这样的标准来组建家庭,可能更合理。
在这样的观察与揣测中,我离她越来越远——就是那个有着方块形冰凉牙齿的她。我最后采用的办法有些疯狂。
我将储存在口腔里的形状与触感“吐”出来(“吐”当然是一个比喻,不然我没法用技术语言向你解释),吐给我的牙医,求她帮我定制一副牙套。正常做牙套要先取模,一般是两个人(戴口罩的神秘女医生和她那侍妾一般的女助手)把你放倒在椅子上,像色情片上演的那样绑住你的手脚,拿敞口钳撑大你的嘴,把你做成一个很搞笑的样子,然后往你嘴里灌满食用硅胶(像在刑讯逼供),等胶凝固了,下死力抠出来(和做空心砖的原理一样)即可。我的办法要稍复杂一些,我为此比正常时间多等了一个礼拜。
我戴上了这副牙套,我模拟她的牙间距与咬合关系,复制她的牙部结构,进而改变我的口腔与发声方式……我会无限接近她,甚至变成她。寻找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变成TA。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会像照镜子一样辨认出彼此。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街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两两相望、互相询问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从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谈崩过,这只是一种程序性的确认。确认后,两人就卸下面具,摘掉帽子和眼镜,脱去全身衣服,赤条条站到对方面前,深情对视。有时一下对不准,两人会稍稍调整一下眼睛的角度,重新对;对上了,就叮一声响,将一生记忆交付对方。
从此再不相见。

姬中宪,1978年生于山东,现居上海,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天涯》《作品》《山花》等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花言》《我不爱你》《阑尾》、短篇小说集《一二三四舞》、非虚构作品《缓慢而永远》、杂文集《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曾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中骏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最佳读者印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