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非虚构丨邱华栋:北京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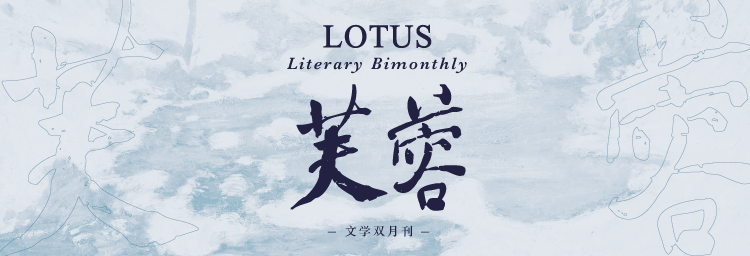

北京传(下)
文/邱华栋
第七章:清京师
八旗内城与民人外城
清朝的北京以及附近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分为京师、顺天府和京县三个层次。
京师是首都的意思,指的就是北京城区,从外向内,包括了近郊、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一圈套一圈。顺天府,在清代管辖有二十四个州县。首先下辖了两个京县,也就是直辖县,这两个县的地位比一般的县要高,分别是大兴和宛平,大兴在东,宛平在西。其余所辖的州县还有通州、霸州、蓟州、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三河、武清、宝坻、良乡、房山、香河等县。
所以,京师指的是当时北京的清代都城地位。但这座京师之城,在一般人那里还是俗称北京。
清朝的特点是沿袭旧制,包括营建皇城和宫城的基本理念,也吸收了明代的经验。满人入关之后,清朝皇帝全盘接收了明皇宫和宫城,大的建筑空间格局基本没有变。但因明皇宫和宫城内的一些建筑曾遭到毁坏,也需要修缮。李自成离开北京之前,曾下令焚烧宫殿和九门城楼。不过,根据历史资料来看,李自成的士兵放火焚烧所导致的破坏,并不是毁灭性的,可能烧毁了部分殿宇,其具体情况如何不详。
一般认为,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因时间仓促,对宫城的焚毁并不严重,只有皇极殿等一些殿庑遭到了毁坏,紫禁城内大部分建筑尚且完好。因为清顺治皇帝登基大典是在皇极门举行的,说明当时皇极殿已经损毁了。
清朝皇帝入主北京皇城之后,没有改变总体格局,但在二百多年间不断重建、翻修和局部整修宫内的各个建筑。现今故宫里留下来的建筑,大部分都是清代建筑,明代原建的已经不多。
在清代,北京城的主人换成了满族人。那么,在对城市空间的使用上,满族人的利益是要优先保障的,满族人的活动空间自然是要优先来安排的。于是,清朝前期,皇帝就把绝大部分汉人迁居到外城,内城全部由清八旗满人居住。
清八旗在内城中都有自己的片区,围绕皇宫,以紫禁城为绝对核心,以中轴线为南北轴线,按照逆时针旋转的话,依次排列如下:
在现今天安门南侧到建国门以西,是正蓝旗满人居住;朝阳门以西,是镶白旗满人居住;东直门以西,是正白旗满人居住;安定门以南,是镶黄旗满人居住;德胜门以南,是正黄旗满人居住;西直门以东,是正红旗满人居住;阜成门以南,是镶红旗满人居住;西单牌楼以南,是镶蓝旗满人的地盘。这样,清八旗满人就把当时北京的内城全占满了。这八旗紧紧围绕着北京皇城和宫城的紫禁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开始修建圆明园护军营房为止,八旗开始向城外新建的旗营转移。
北京有句俗语“不问满汉,但问旗民”,指的是内城的旗人中也有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甚至还有俄罗斯族的旗人佐领。民人都在外城居住,其中汉人居多,也有其他民族的人口。
外城,就是现今前三门大街以南、一直到永定门南北一线的南城,就是“凸”字形凸出的区域。外城也分区域,从东往西分别为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个区域。在清代中期之前,北京地域文化由内城的八旗文化和外城的汉人文化构成。外城的汉人文化,也称为“宣南文化”,泛指宣武门之南的汉族市民文化。
内城因为包裹着清皇城和宫城紫禁城,是绝对的权力中心,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没有固定住址,不得夜宿内城。只有一些寺庙和八旗中的汉军军营里的汉族士兵,可以住在内城区域里。
一些汉族士大夫,尽管属于参与了清代社会管理的上层阶层,也住在外城区域。围绕着这些人士的宅邸,逐渐就出现了新型的宣南文化。
在清代开国时期,出现了八个号称“铁帽子王”的满族皇亲家族,也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王府,建在内城之中,一般在紫禁城中轴线向北延伸的两侧区域里分布。这八位清代开国时期分封的“铁帽子王”如下:
礼亲王代善,王府在大酱坊胡同;郑亲王济尔哈朗,王府在大木仓胡同;睿亲王多尔衮,王府在南池子;豫亲王多铎,王府在帅府园胡同;肃亲王豪格,王府在正义路;庄亲王硕塞,王府在太平仓胡同;克勤郡王岳托,王府在新文化街太平桥大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王府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这八位“铁帽子王”因对清代开国有功,属于“世袭罔替”,不需要后代降级继承亲王的爵位。
后来,在雍正、同治和光绪年间,因各种原因,又封了四位“铁帽子王”,也是“世袭罔替”这一级别的亲王,如下:
怡亲王胤祥,王府在王府井东冰渣胡同;恭亲王奕,王府在什刹海西南角;醇亲王奕,王府在后海北沿;庆亲王奕劻,王府在定阜街。这些满族皇亲宗室,以他们的权力形成了向外不断扩展的血缘、宗族的势力依附圈层,成了北京城的新主人。
清代土地的占有形式分为皇庄、王庄和旗地,土地的买卖也伴随着人口的移动。到清代后期,也就是从公元1860年,以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作为标志,旗人住内城、汉人住外城的规矩打破了。因外城在汉族人和其他民族人口的经营之下,非常繁华热闹,汉族精英也不断进入清朝统治阶层,因此也被分配在内城居住。同时,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贫苦旗人不断出现,他们搬出内城,住在了传统汉人居住区的外城。
还有的旗人变卖了城内宅基地,迁居到了北京的近郊和远郊,买下一些田庄、皇庄,雇佣汉人作为佃农。另外,八旗军营也不断向城外迁移,如蓝旗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锐健营等,都是后来迁出内城的八旗军营,北京城市空间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到了清代后期,无论内外城,满、汉和其他民族的混居就比较普遍了。
另外,清代北京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大运河的漕运。清代依赖两湖地区的稻米,和中原地区的小麦等农作物粮食。清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进行了一次城市人口普查,当时北京内城人口45万多人,外城人口30多万,合计76万多人。这还只是常住人口,每天的流动人口可能更多。这么多人每天吃粮,大都需要外运。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大都存放在通州的粮仓,再通过马车运到东便门的大通桥,放在东墙外的粮仓,也分送各个内城区域的粮仓。通过现今还存在的南新仓、禄米仓等地名,依稀能够看到这一历史由来。
宫城皇城大城
清代的京师北京城,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功能就围绕着这一中心功能在运转。
在清代,在宫城内建筑营造上,大格局维持明代规制,具体的建筑做了很多的修缮、改造乃至重建,因宫城内,特别是大内紫禁城的主要建筑都是木质的,容易在时间的作用下虫蛀和自然坏朽,加上日常使用的耗损、雷火导致的火灾威胁,时不时要进行维修。
因而紫禁城的修缮和改造是持续进行的。顺治朝时期,将前朝大殿和后宫嫔妃们居住的宫殿修造完毕,使宫城能够正常使用,康熙年间将宫城恢复到了明代鼎盛时期的建筑规模。乾隆年间在宫城内修建了一些新建筑,如文渊阁、宁寿宫、重华宫等,这些建筑打破了明宫城内的对称格局,填充了宫城建筑空白点,使宫城空间利用得到了新扩展。
这就像是明式家具的风格极其简约,而清式家具就变得繁复起来了。我们观察清代家具,在装饰上非常雕饰、极尽华丽,细节上更为机巧和繁复,清代对宫城建筑的雕琢是很耐心细致的。
有些雷击导致的火灾未能避免,但所有的宫殿建筑,都经受住了北京多次地震的考验。这其中,斗拱在木结构的建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斗拱位于立柱和横梁之间,既有承重作用,也有装饰作用,使得木质建筑具有了受力弹性,有了伸缩度和柔韧性,这是宫城建筑经受住地震考验的关键原因。斗拱这一中国建筑文化的杰出创造,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学会的会徽图案。
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是北京城的核心,紫禁城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在大内宫城中,是怎样活动的呢?我在吴十洲先生所著的《乾隆一日》中,看到了乾隆皇帝一天里事无巨细的详细活动。
吴十洲的这部书挑选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765年1月28日。这一天非常普通,在《清太宗实录》中,只有几百字的记载,但吴十洲却用了28万字的篇幅,详细描绘了乾隆皇帝的普通一天。
根据时间线索,我们能看到乾隆皇帝一天里的时间安排:
凌晨4点,乾隆皇帝起床。养心殿请驾,更衣。然后去坤宁宫朝祭。5点,饮冰糖炖燕窝。6点,在中南海同豫轩进早膳,之后去乾清宫西暖阁看前朝圣训。7点,更衣,在建福宫稍坐,去重华宫茶宴,邀请臣子在重华宫对诗联句。10点,赴养心殿勤政亲贤殿批阅奏折,一直忙到12点之后。13点钟,在养心殿前殿引见臣工,14点继续在养心殿引见臣工,并进晚膳。15点小憩,批阅内阁呈上的各部和督抚、提镇的本章。下午4点,与傅恒“晚面”。傅恒是首辅大臣,也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傍晚17点,在养心殿三希堂等处鉴赏文物。18点,继续在养心殿三希堂鉴赏文物。19点,小憩。20点,养心阁后殿东暖阁就寝,入眠。
这只是乾隆皇帝在紫禁城里这一天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一整天安排得非常满,每一个时辰都有十分具体的事情要做,其中,对诗联句是有臣子参加的,批阅奏折需要好几个小时,欣赏文物的时间也比较充足。他早起早睡,几十年来每天如此,是一位十分勤勉、勤政的皇帝。
在宫城内,是内廷围绕着皇帝每天的活动而细密地运转着。紫禁城的外面,包裹着的皇城里,又有什么变化呢?
在清代,皇城所开的大门在名称上有些变化。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建筑规制是三阙之上为飞檐高脊,这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往南的承天门在顺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651年改为天安门。在天安门里,是“左祖右社”建筑,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
皇城里的组团空间结构,主要有宫城、太庙、社稷坛,还有北部的景山与西苑花园。除此之外,皇城之内分布着重要机构衙署。明代分布的二十四衙门,到了清代中期后基本废弃,都由内务府所辖的“七司三院”占据,内务府规模扩大,它负责整个清代皇室和皇宫日常生活的供应。这“七司三院”分别是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和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这些司和院掌管着皇城内的很多仓库,现今还有些地名就是当时皇家仓库的地名。内务府仓库的分工很细致,哪个库摆放哪个东西,都很具体。防火、防盗措施也很多。
清代皇宫内还有六部机构和建筑衙署,吏部、礼部、户部、刑部、兵部、工部;五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三院,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等大量衙署。这些衙署建筑,集中在千步廊的两侧。
相比明代,皇城内缩小了宫苑和官署的范围,空出来的地方就变成了佛寺和民居。清代的皇城里寺庙也不少。现今记录有兴隆寺、华严寺、玉皇庙、普渡寺、延寿庵、慈云寺等二十多座,其中有少量的道观和尼姑庵,这些寺庙大部分都曾是明代衙署建筑。因清代皇帝也推崇佛教和喇嘛教,在皇城内几乎处处可见寺庙。
皇城内还有很多民居,这一点和明代不一样。明朝的时候,皇城之内是没有老百姓居住的,在清代,大内紫禁城里是皇帝专属的活动区,但宫城外的皇城里,却有很多王公贵族和一般百姓居住,还有八旗旗人的居住区。这些官员、市民、士兵、商贩,都游走在皇城里,除了宫城和西苑、太庙和社稷坛之外,他们能够在很多区域里活动,商业发达,人员众多,相对自由,使清代的皇城体现出一种少有的城市活力。
如高士奇在他的《金鳌退食笔记》中所记载:
“紫禁城外,尽给居人,所存宫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时严肃禁密之地,担夫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
可见,清代皇城内的生活化场面很生动。
北京大城中,内城旗人的八旗和外城的民人生活区,两片区域的生活面貌迥然不同,构成了不一样的文化习俗,彼此影响、互相塑造,是有清一代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北京的八旗文化,可以说上承清朝的皇家文化,下接北京的民间世俗文化,两百多年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清朝覆灭之后,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整理和关注非常不够,只是在近些年,学者对北京八旗文化遗存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整理。
在外城的汉族士大夫、文化精英以及民人百姓所共同铸造形成的“宣南文化”,也是清代北京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北京外城出现了很多会馆。因全国各地都有地方官、商人和士人,频繁往来于家乡和北京,他们在北京的留驻之地,就是外城区域的各地会馆。
会馆文化的形成,是这一时期北京城市文化的一面风景。北京现今还有湖广会馆建筑留存,是民间相声、曲艺表演的场所。在清代,内城开设的旅店、饭馆较少,大部分旅店、饭馆就开在了外城。由于清代国土辽阔,省份数十个,乡土情怀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结,各地人士纷纷在京设立会馆,就如同现在各地在京设立驻京办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的驻京办是各个省市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当时的会馆,则大都是商人在经营,这些会馆背后的操纵者和出资人,往往又是当朝的官僚和有钱人。
会馆中供奉有关帝、财神、真武大帝等等神灵保佑大家。所以,会馆有着精神、感情、宗教和地域文化的联系与寄托。此外,大的会馆之内如湖广会馆,还搭建有戏台罩棚,演戏、喝茶、吃饭、交流就成了会馆的最重要功能。这一时期,同业行会也在会馆的串联之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清代民间商业的发展。会馆也带有行业的地域性,造就了一些行当的富人,他们逐渐买下内城落魄旗人的地产,影响也渐渐扩大到了内城。
京城会馆的出现,是当时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表征,促进了清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流动,也加速了人口的流动。根据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一书的记载,外城中的东、西、中、南、北这五个城区中,大大小小的会馆接近四百个,这些会馆终日里都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官员、商人、举子,来朝廷汇报工作的外地官僚,来北京投亲靠友的人,大家都操着方言,在外城的城区到处走。这样的情景反映出清代北京的包容性,和首都地位的强化与提升。
清代北京的商业中心转移到了前门大街一带。前门大街现在也是南城的繁华之地,西侧是大栅栏,东侧是鲜鱼口,聚集了大量的商贾店铺。宣武门外有菜市口,崇文门外有花市,还有琉璃厂的文化市场和前门外的“八大胡同”这样的香艳之地,外城的市井俗文化和士族雅文化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外城日常生活的鲜亮色彩。
清末北京流行一种说法,叫作“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说的是北京大城东边住的是富人,西边住的是贵人,南边住的是贫民,北边住的是贱民。清代末年,大城区域之外,在北京近郊又形成了一些新居民区。
这种说据说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当时是形容内城的居民格局。大运河的漕运造就了富裕的商人阶层,他们大都住在东部城区。到了清代,城东的仓库很多,商人也多聚集在东城,漕运依然发达。
特别是到了清末,大城南部住了不少城市贫民,在大城以北有很多坟地,还有太监、佃农居住区,捡破烂的、流浪者等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也生活在那里。所以,“南贫北贱”就流传开了。这种说法朗朗上口,是对当时大城居住人口的形象描绘,是清代末年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变化。
三山五园
清代对北京空间结构营造的最大贡献,是西郊皇家园林的建设。
因清代皇宫沿用了明皇宫,除了新建和改建了一些建筑,宫城也不断修葺,明代留下来的城市总体格局不变,城内没有较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当然了,清代在内城新建的亲王府、在郊区营建的皇家园林、离宫苑囿和八旗军营,都是有清一代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拓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和建筑奇迹。
清代与明代迥然不同的一点是,清代朝廷的政治中心不仅在紫禁城,西郊的皇家园林也是政治中心之一。也就是说,由于“三山五园”的存在,有清一代实际上有两个政治中心,清代的皇帝在紫禁城和西郊“三山五园”中的离宫这两个地点,决策着国家大事。
在清代皇家园林的营建中,以“三山五园”的建设成就最有代表性。“三山五园”是清廷的离宫别苑,它的建造时间主要在清代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朝年间持续进行。这几位清代初期的皇帝,为“三山五园”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精力和财力,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此外,清代在承德修建了离宫避暑山庄,这也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离宫别苑。
皇家园林建设的根本理念,在于“移天缩地在君怀”,将天地间的精华景物缩小在眼前,天之骄子皇帝穿行于其间,人在园中,天地也在心中,这是中国古代君王追求的至高境界。从汉唐时期的皇帝建造离宫,到宋徽宗营建艮岳,都是这一理念的外化。
“三山五园”是老百姓对清朝在北京西郊营建的皇家园林的通俗说法,未见清代文献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到底是哪三山哪五园,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来说,三山,指的是瓮山(后来改名为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瓮山是在公元1750年、乾隆十五年改为万寿山的。
五园,指的是哪些园林,争议就比较大。根据现在一般的看法,五园是圆明园、畅春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
有学者认为,“五园”是单指圆明园中的五园,就是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园。
不管如何争论,“三山五园”是人们对清代西郊皇家园林的总体称呼,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具体地分辨到底是哪五个园。我采取前一种说法。因为圆明园中的五个园,建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三山五园”就是三山含三园,另两个园分别是圆明园和畅春园。
清代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中,三山基本上在同一纬度线上,从西到东,分别是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五园中另外两园,圆明园和畅春园,在这片西郊皇家园林的最东端。这使得北京城形成了西郊一线、横亘东西的园林之最,作为离宫别苑,与北京皇城构成了一体两地的格局。
这“三山五园”在清代不光是供皇帝游玩散心的地方,我在前面说了,它还有政治中心的意义。每年的某个时段,清朝的皇帝在“三山五园”的某处待的时间,要比他在紫禁城内待的时间还长。往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皇帝都在这西郊离宫处理政务,这时,西郊的皇家园林就成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在清代早期,顺治皇帝时期,西郊皇家园林还没有修建,他一般喜欢去南苑和西苑这两个规模较小的离宫苑囿。西苑是中海、南海、北海三海的总称,非现在北京西苑的所在。南苑之地相当开阔,是一片狩猎的野地,顺治可以在那里骑马射箭,获得军事训练的乐趣。
从康熙朝开始,西郊皇家园林开始营建。建成的畅春园是康熙皇帝最喜欢居住的离宫苑囿。
畅春园原来是明代武清侯李伟别墅的一部分,后来建为畅春园,在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第一次驻跸畅春园,就很喜欢这里。公元1691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一下住了四个多月。可以说,这时清廷的政治中心就变成畅春园了。因此,研究清代政治历史,关注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历史作用,也是考察清代政治运作的观察视角之一。
圆明园可以说是清代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首,冠盖五园,它是于康熙四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07年全面建成的,康熙将这座园林赐给了儿子胤禛。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即位之后继续扩建圆明园,圆明园成了雍正最喜欢的离宫,因此也是雍正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北侧修建长春园,又把熙春园划归圆明园,改建绮春园。公元1782年,他将淑春园改为春熙园,这样就形成了圆明园之内连体共生、璀璨繁华的圆明园五园。每年,乾隆皇帝要花四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圆明园居住。这是圆明园达到最顶峰的时刻,只要乾隆皇帝在圆明园,这里就是清朝的政治中心。
再来看看玉泉山的静明园。金代的金章宗喜欢游山玩水,他在玉泉山修建了行宫芙蓉殿,并创造出“燕京八景”的提法。其中的“玉泉垂虹”描绘的就是玉泉山的景观,后来芙蓉殿遭到了毁坏。元代郭守敬曾引玉泉山的水变为金水河进入元大都宫城,最终贯通了通惠河,说明这里的水资源十分丰富。
在清代,玉泉山这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自然就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了。玉泉山现存一座玉峰塔,远远地就能看到。玉泉山静明园是从康熙十九年营建,到乾隆年间最终建成的,内有玉泉十六景,可见玉泉山的山、水、泉、塔共同构成了一幅静明园的美景。
香山静宜园是最靠西的一座皇家别苑。金世宗曾在这里修建大永安寺,这是后来香山寺的前身。乾隆年间,在康熙修建了香山行宫的基础上建成了静宜园。乾隆还给静宜园命名了“静宜二十八景”,可见香山静宜园有着一种别处没有的精致之美,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对静宜园的重视和喜爱。
乾隆皇帝命名的“静宜二十八景”,细数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些景名起得灵气飞动。这二十八景有绿云舫、丽瞩楼、璎珞岩、翠微亭、玉乳泉、知乐濠、香山寺、芙蓉坪、栖月崖、玉华岫、隔云钟、蟾蜍峰、青未了、驯鹿坡、听法松,等等。足足二十八景,可见乾隆皇帝的用心良苦和静宜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现今去北京植物园游览的话,还能看到当年静宜园的气韵。
以上的皇家园林,除了玉泉山静明园在清代重修之后,留下了相对完整的规模外,还有万寿山清漪园能够让我们一窥“三山五园”的气魄究竟。万寿山清漪园,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昆明湖风景区,这是北京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西郊皇家园林的代表作。
清漪园修造完成的时间比较晚,是在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为母亲六十大寿祝寿,特地修建了清漪园。为此,他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把翁山泊改为昆明湖。清漪园的最大特点是水面特别大,虽然有着江南园林的细节,比如西湖苏堤的挪移变为长堤,但在现今的颐和园,却呈现一种狂野、开阔的北方园林风景的明朗之美。
万寿山上的佛香阁,至今仍是颐和园的最佳观景点和重心所在。清漪园或者说颐和园,它的建造也要追溯到金代。早在海陵王完颜亮从会宁迁都到金中都、现今北京的时候,他就在此修建了行宫。
现今的昆明湖,在元代郭守敬疏浚河道时还叫作瓮山泊。万寿山一直叫瓮山,山脚下的一汪水面就是瓮山泊了。
“三山五园”命运多舛。公元1860年10月6日,也就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后,放火把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一起都烧了。那一次的大火,一连烧了三天,“三山五园”最后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重修了她最喜欢的万寿山清漪园,并将重修后的园林改为颐和园。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了这里,这一次,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也都遭到了彻底破坏。不过慈禧太后再次修复了颐和园,足见这座园林对于她的重要性。不惜动用军费来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以供享乐,距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圆明园至今仍是废墟一片,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我们现在去圆明园遗址,看到的是令人痛心的一幕。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记录着清末衰弱的国家所遭受的惨痛打击,至今裸露着巨大的历史创伤。
现在的畅春园的区域,在北大校园和家属区中。未名湖周边,依稀可见畅春园的痕迹,现存有“畅春园东北界”石碑桩,恩佑寺和恩慕寺的山门等古建筑遗迹。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畅春园在北大校区的痕迹、圆明园废墟、万寿山清漪园改叫颐和园的昆明湖景区。
香山静宜园还有少量留存的遗迹,玉泉山静明园经过了清代重建,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景观,现为干部休养所,不对外开放。好在颐和园今天保存完好,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千万普通的中国人游览和喜爱。
除了上述的北京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清代对南苑的营造也应该着重写上一笔的。细说起来,康熙皇帝出宫喜欢住在畅春园,雍正和咸丰皇帝都喜欢把圆明园作为他们的离宫,而比他们都早的顺治皇帝,当初刚刚入关后,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都还没有影子呢,怎么办?顺治就造了一个南苑。他最喜欢的离宫,就是南苑了。
南苑距离永定门十公里左右,作为清初的皇家园林,面积相当大,约有200平方公里。整个南苑都由围墙围了起来,一共开了九个门。在南苑之内一共建有四座行宫,分别是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团河行宫和南红门行宫。
南苑的北门是正门,叫作大红门,皇帝一般从这个门进去。南苑和“三山五园”最大的不同,在于南苑是清初的皇家狩猎场。因满族人本来是渔猎民族,骑马射箭是基本功,他们入关后统治中国,也没忘记这个基本功,于是顺治皇帝就喜欢在南苑骑马射箭。
南苑地域广大,野气纵横,适合训练和检阅军队,后来康熙皇帝也在南苑阅过兵,接见过少数民族部族首领来朝。乾隆朝之后,南苑的地位就下降了。
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朝廷卖掉了南苑的土地,这块土地由皇家苑囿之地,变成富人阶层可以买来盖房子、建庄园的地方了。南苑的皇家别苑和狩猎场、阅兵场、行宫的地位,从此不存在了。
20世纪中,这里有一座南苑机场,南苑的地名因此而继续存在。后来在兴建北京第二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规划中,把南苑机场合并到了新机场的区域里。2019年底,随着大兴国际机场的正式启用,南苑机场也同时关闭了。
今后,这里将兴建一座南苑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北京南中轴线上的一座生态园林明珠,和南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景观带。
副章:恭王府与东交民巷
恭王府花园
在清代,顺治六年将宗室的封爵分为十二个等级: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对于这十二等爵位的皇亲国戚府邸的建筑规制,包括建筑符号、标准和材料,都有详细的规定,不能逾制。
因此,王府是皇宫和民居之间的一种建筑。
在这十二个等级的府第中,亲王府邸的建筑规制最高:正门五间,启门三间,并以坚固的高墙为院墙。正殿七间,翼楼各九间,后殿五间。后寝七间,后楼七间,府邸一共是五重。
清代的王府建筑,一般分布在内城南北中轴线两侧的城区里,成为封建等级秩序中的礼制建筑。虽然王府有限制性规制,但在建筑营造上,也有很多别具匠心之处,成为清代北京城市营建中的一大亮点。不过,王府的产权在朝廷,有的是世袭罔替,还有的是世袭递降。递降,就相当于官邸制,王的爵位没了,再好的宅子也会被皇帝随时收回,然后赏赐他人。
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明的王府,一共有42处之多。到了清嘉庆年间,北京的王府府邸已经达到了89处。现今北京留存下来比较有名的王府旧址有醇亲王府、孚郡王府、雍亲王府、礼亲王府、庆亲王府、淳亲王府、顺承郡王府、恭王府等。其中,恭王府在这些清代的王府中最有代表性,几经修缮,也最漂亮,有关它的故事也最多。
恭王府花园如今是游赏北京的一个好去处,它是北京现存的王府中名气最大的一个。恭王府花园位于什刹海前海三座桥的西北面,曾经是清代末年恭亲王奕的宅子。这所王府花园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恭亲王的特殊政治地位,还在于它的前身是乾隆朝的宠臣和珅的大宅子。
和珅尽管很受乾隆皇帝宠信,但他只是朝臣,不是亲王一级的皇亲国戚,修建自家宅子的时候,就不能按照王府的规制来营造,宅子的大小、房间的面阔、屋顶的规制等,都不能僭越规制。但他后来倒台了,其中一项罪名,还是因为“僭越”。
和珅担任过的官职爵位很多:封一等忠襄公、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等,他还兼任过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兵统领等,这一箩筐的职务都是要职,可见他深受乾隆皇帝的宠信,权势熏天。
和珅当年盖的宅子门脸不是亲王府的门脸,最大的看点在后花园,别有洞天。和珅后来在嘉庆皇帝初年倒台,不仅人头落地,还被新皇帝抄了家。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他免不了的命运。当时,和珅的一大罪状,就是建筑府邸逾制——他用了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金丝楠木,“其多宝格及隔断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仁宗实录》)。就是说,他按照紫禁城宁寿宫和圆明园蓬莱瑶台的规制,来建造自己的房舍和后花园,那是大大的逾制和僭越了。在古代中国,僭越是一个大忌,在和珅的二十大罪状里面,这府邸营建的僭越也是一大罪状。
和珅府里的贵重东西都被新皇帝派人抄走了,这个宅子也被嘉庆皇帝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庆郡王永璘。但当时和珅的一个儿子已经和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结了婚,他算是“额附”,在皇家地位等级上,不低于这个庆王永璘,因此还能住在这里。那么有段时间里,这个宅子就是一家一半,两家分着,一墙之隔住在里面。又过了三年,到了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的时候,和孝公主死了,宅子就全归永璘家了。此时,庆王永璘已经去世3年多了。
前面说了,清代施行的爵位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世袭罔替,就是开国的八个亲王加上后来增加的恭亲王等四位亲王,子孙不减待遇,因此叫作“铁帽子王”。另外一种是世袭递降,后一代比前一代爵位要降低等级。
永璘的孙子就降为了辅国将军,不能再享受王府待遇了。到了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这所宅子就由咸丰皇帝赐给了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
相传,恭亲王奕喜欢《红楼梦》,他先是把后院扩大,圈进来不少民宅,然后让人按照《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意境,请工匠按图索骥,进行营造。于是,工匠在恭王府后花园萃锦园的别致空间中,加了大量的水景、游廊、亭台、花榭,使恭王府成了一座园林建筑和别有洞天的王府花园。
周汝昌先生为此专门写过《恭王府与红楼梦》一书,专门表达自己的发现。不过,我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对建筑的描写也是虚虚实实的,故意不写出所处时代的特征,让你看不出来到底是明朝还是清朝,非清非明,似清似明。人名、地名、官职、服装,都是这样。这是曹雪芹高妙的地方。在建筑形制的描写上,也是如此,如他在小说第三回中描写王府的一段:
“……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正门却不开,只见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
如果这一段是实写清代的王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就不合规制。因清代王府门前的石狮子不临街,临街的是东西阿塞门,石狮子在阿塞门内,不是一眼就能看到。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建筑描绘,也是虚实相间,虚虚实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阅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因这座王府花园的主人,先后有权臣和珅、和孝公主、庆郡王永璘、恭亲王奕、奕的孙子、末代恭亲王溥伟,这一大串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都在这座宅子里生生死死,自然给王府花园增加了很多历史和文化内涵,他们演绎了多少宅子和人的命运的故事啊!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成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的女部。
恭王府的历史价值、建筑文化价值都很高,有人夸赞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此言不虚也。
恭王府建筑分为王府府邸建筑和花园园林建筑两部分。按照《大清会典》中的规制要求,王府的府邸建筑分三路,中间的主路是主体建筑,屋顶可以覆盖绿色琉璃瓦。绿色琉璃瓦具有礼仪和祭祀的功能象征,整个恭王府的主路建筑是庄严、气派、宏伟的风格。正门叫作头宫门,正殿是银安殿,殿内放着亲王宝座,宝座后面有八尺高的三折大屏风,屏风上绘了金色云龙图案。
东西两路是两进的院落,嘉乐堂在恭王府内是举行萨满教祭祀仪式的地方,后楼就是后罩楼。恭王府后罩楼辉煌气派,共有两层,长达160米的转角楼,多达四十七间房,号称九十九间半,说的就是这里。它横亘在整座王府的后花园之前,既是收尾,也是绝佳的屏障,雕梁画栋,红漆柱子,窗棂精美,传说当年和珅的大量珍宝都藏在这里。楼的底层正中有堂门,直通后花园萃锦园。
萃锦园是恭王府花园的园林部分,也是这座王府建筑的精华所在,能够看到清代造园的很高水平。萃锦园与它南部的府邸相对应,也分东、中、西三路。真的是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万千气象、花团锦簇。
恭亲王之子载滢曾写了《补题邸园二十景》,详细描绘了萃锦园的二十处风景:曲径通幽、垂青樾、沁秋亭、吟香醉月、踨蔬圃、樵香径、渡鹤桥、滴翠岩、秘云洞、绿天小隐、倚松屏、延清籁、诗画舫、花月玲珑、吟青霭、浣云居、松风水月、凌倒景、养云精舍、雨香岑。通过这些别具韵味、对萃锦园高度凝练式概括,我们应该能想象萃锦园的万千景致,是如何乱花迷人眼的。
萃锦园中路从一个园门进入,是三进的院落,有青石假山分列两旁,叫作垂青樾和翠云岭。青石假山向东西两边延伸,把萃锦园环抱起来。往前走,就是曲径通幽,正厅安善堂端坐其中。
继续前行,那二进、三进的院落,不断把各种景致都点缀在这个花园的不同空间中,精粹而华美,柳暗而花明,层峦而叠嶂,美不胜收。这些词语形容这中路三进院落中层层递进的风景之美,丝毫不夸张。
东路的三进院落边,有一座竹林边的大戏楼,这是恭王府花园的一大亮点,现今北京听戏的地方,有两处最有名:一处是湖广会馆,另外一处就是这恭王府的大戏楼。真戏迷,一定去这两个地方听过戏。
西路的主景是一面长方形的水池,波澜微惊,春水乍起,长长的游廊蜿蜒游走在边上,一座土山将之环抱,使你感叹这恭王府花园实在是有容乃大,山重水复,冬去春来,生生不息。
东交民巷
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建筑格局与符号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展开,清代末期北京的建筑风格也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在这个使馆区中出现了很多西洋风格的建筑,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淘洗,仍旧有很多当年的建筑保留了下来,成为北京昔日旧影中一抹独特的光亮。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元代这里就通行漕运,郭守敬沟通的运河水道使得漕运很方便,这里设有一座河道的水关,南方运来的大米都在这里卸货,政府也在此设立了收取大米、糯米税的税司。糯米在北方人的发音中叫作“江米”,所以一开始这里叫“江米巷”,分为东西两段。
明朝时期,这一片区域就变为了皇城的前部广场,在现今天安门广场以东,分布有很多衙署。东交民巷这一片分布有礼部和鸿胪寺,这是当时专门分管外交和民族事务的国家机构。
后来,在公元1840年,清朝设立会同馆,用来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来访的宾客,隶属礼部管辖。会同馆的位置就在东交民巷北面的御河桥西一侧,会同馆是清代进行外交活动的机构,这是东交民巷演变为使馆区的前因。
公元1860年10月25日,咸丰皇帝签署并公布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里,其中有一条,是准许英国和法国派遣公使前来北京进驻。这对于清朝这样一个封建王朝来说,还真是一个接受起来十分为难的难题。此前,并无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外国人在清代朝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是很让人不放心的。但这一次,是在清廷战败之后签订的屈辱条约,必须要执行。于是,按照条约内容,英、法外交官很快就来北京驻节了。
英国公使当时是额尔金,他选择了东交民巷的梁公府作为英国驻华使馆。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大宅子,位于御河西岸,一道御河成为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恭亲王奕照会额尔金,说这房子可以租用为英使馆,但英国人每年得支付一千两银子作为租金,按年支付。前两年的租金作为修缮费用。
额尔金同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转眼到了公元1861年3月,英国首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先生来到了北京,正式进驻使馆。
接着,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到任北京。法国使馆也是租的,位于台基厂南口,东交民巷路北侧,是原来纯公府宅邸,局部损坏严重,西墙都倒塌了。经过商议,奕同意法国人在纯公府西花园的空地上盖新房子。
同年,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任,入驻御河西岸边的俄国大使馆。这个使馆紧挨着英国使馆南侧,在东交民巷的北侧。这是公元1861年间,英、法、俄三个列强国家的使节率先入驻北京使馆的情况。
从公元1862年到1873年,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日本和荷兰等国,也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这些使馆大都位于东交民巷附近,以御河为参考点,在东交民巷路的南、北、东、西,几个方向延伸开去,次第修建而成。东交民巷使馆区就初步形成了。
公元1900年庚子之乱前后,东交民巷使馆区在受到破坏之后得以更大规模地重建,形成更加完备的外交使馆区域,这是北京这座京师皇城的城市空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群,从此成为清末北京城市建筑的新符号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附着了政治、文化、外交等多重意义的建筑群,值得仔细探访。整个东交民巷使馆区占地约100公顷,约等于紫禁城的一倍半再大一点。在这个区域里,按照清末的外交条约,设立使馆的各个国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进行规划设计,自行建造使馆内的房屋。于是,各种风格的使馆建筑就拔地而起,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世界博览会般的建筑群,成为清末北京对外开放交流的观察点,也是观察清代北京建筑空间变化的绝佳窗口。
东交民巷所处的地域,是清代皇城外围的重要区域。比如,在英国使馆和俄国使馆的西侧,就紧邻着清代的皇家机构宗人府,以及一些重要衙署,如吏部、户部、礼部等中央机构的衙门。现在,这一片区域被确定为“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受保护的北京市建筑文化遗产。
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义和团拳民摧毁了不少使馆区的建筑,其中,英使馆受到的损失最大,也包括几所教堂。但这些教堂在第二年就重建了。后来,按照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不能有中国老百姓居住,使馆封闭式管理,戒备严密,成为一座城中的法外之地。
东交民巷使馆区修建了一道围墙包裹着使馆,围墙的外面还有一条深深的壕沟。现在信步走在东交民巷,那些老建筑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你,每一幢建筑的背后都有着独特的故事,等待着你去发现。
东交民巷不仅是外交使馆的集中之地,在清代末年,这一带还是各国的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国际饭店、医院等汇聚的地方。特别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如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等大银行的总部也设在这里,这些大公司富可敌国,有的银行至今还是国际金融业巨头。当时留下的建筑,现在你去观察,是可以和上海外滩的那些外国金融、商务机构的老建筑相比较的。
漫步在东交民巷,可以看到这片区域以东交民巷和玉河为十字交叉,形成了东、南、西、北四片更小的区域,当年那些使馆和金融机构的老建筑,大部分都是两层或者三层的洋楼,并不高大,但也有例外,如圣米厄尔教堂的哥特式尖塔依旧十分醒目,它建于公元1901年,是北京地区最小的一座天主教堂,由法国高司铎创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奥匈帝国率先放弃了驻华使馆,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这片使馆区内的列强们设立的使馆使用权,陆续被中国政府收回了。
现存的建筑中,法国公使馆旧址后来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其夫人在京的临时住宅。原英国使馆内的武官楼气势非凡,饱经沧桑。它坐北朝南,红色砖木结构,有拱券窗户装饰,柱头为希腊爱尼奥式,在大槐树的掩映之下,别有一种韵味。另外一幢比较有特点的建筑是正金银行旧址。这幢银行大厦是在清代灭亡的前夜、公元1910年建成,设计师是日本建筑师妻木赖黄(也有一种说法,说设计者是妻木赖黄的下属森川范一和松井三吾),风格上融合了荷兰古典主义风格,外立面是红色砖块与白色石材交替使用,转角还有一座塔楼,整座建筑造型风格是坚固、严整而又活泼,现在是这一地区的地标建筑。
徜徉在这片使馆老建筑群中,一幢幢的洋楼静谧地矗立在那里,它们显得老旧、斑驳,非常安静。其中,有很多幢建筑都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就像是历史的无声诉说,和建筑界的世界博览会,这片以西方近代古典建筑风格为主调的建筑群,足够你去尝试着发现北京清末时期的很多耐人寻味的涉外历史。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设,当时也带动了教堂建筑和大学校舍建筑的西洋化。梁思成先生在描述这一情况的时候写道:
“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
那一时期,清华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北京饭店老楼、正阳门火车站等,都是外国建筑师设计或者受到洋风影响的建筑,成为北京城市空间中独特的符号,诉说着这座城市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求索。
因此,无论是建筑背后的政治历史文化符号,还是建筑风格呈现的西洋文化符号,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存在,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摘自《芙蓉》杂志2020年第4期邱华栋的非虚构作品《北京传·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西峡。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教授的黄昏》《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长生》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篇。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