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叶舟:凉州十八拍(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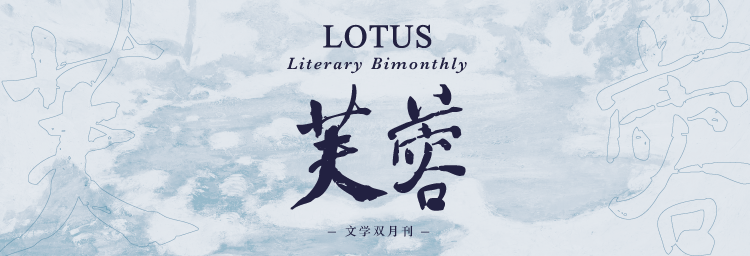

凉州十八拍(第二卷)
文/叶舟
胡笳30节
那日黄昏,顾山农正在堡子外训话,突然发现家里的一名伙计急吼吼地寻来了。
承平堡招募人手的工作,经过了三轮淘汰,进入了尾声。无疑,招募一事,由少东主亲自定盘,设立了相关的条陈,倘若触犯了其中任何一项,一概不录。至于具体的细节,则交给了廖逢节、张汲水和几名权家的心腹伙计。事前,顾山农召集大家面议,实际上是在紧螺丝,丑话撂在了当面,谁要是敢走门子,托关系,徇了私情,他自己的那一只饭钵,恐怕也将端不住了。竖起大王旗,招来吃粮人。招募的消息传布出去后,仅仅在凉州一地,便有成百上千的青壮汉子星夜而至,填报了名姓,等待检录。时至秋末,武威城外五门十八姓的庄稼人,包括远处各个庄子上的后生们,眼看着进入了冬闲阶段,与其天天赌博和醉酒,倒不如去承平堡挣一笔痛快钱,然后过一个肥实的春节。显然,这样的算盘打错了,错得太离谱。承平堡不招短工,讲究的是一个长期效力,终身投靠。粗检了一遍,人数几乎被砍掉了一大半,留在名册上的,方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犹如过筛子一般,异常挑剔。此后,各种传闻不断,全都是牙茬话与风凉话,来自那些被淘汰下来的龌龊鬼,他们指着承平堡的方向,啐干了嘴里的唾沫。有的说,顾山农这是在占山为王,招兵买马,那样的歧途不走也罢,等着看他的可笑吧。另外的更是不屑,什么狗屁的保价局,顾山农还不是开了一家大客栈么,他就想将过境的商团、驼队和马帮拦在城外,入住在他的承平堡,吃独食,挣一些火炕钱和饲料钱罢了。那一阶段,顾山农负谤难明,却也不辩解,不伸张,暗中加快了步伐。
第二轮的名册交在了顾山农的手上,有二三百人,等着他勾画。风向突然变了,顾山农的重点,开始放在以下两类,容不得旁人置疑:其一,凡是在尕司令马仲英的屠刀下侥幸生还,从镇番县的那一场生死浩劫中逃出来的难民,一律优先录用;其二,在前些年的凉州大地震中,从残垣断壁中爬起来的人,眼泪哭干的人,断了炊火的人,同样也在优先录用之列。廖逢节知道少东主的善意,张汲水亦不例外,照此办理去了。名册渐渐地薄了下来,第三轮开始之前,顾山农再次立了几项绳则,不孝者不录,还俗者不录,手脚不净者不录,口敞之人不录,耍赌者不录,酗酒者不录,吃鸦片者不录,打骂牲口者不录,挑是拨非者不录……凡此种种,总计有十七八条,森严不可逾矩。张汲水狐疑道:少东主,其他的我大概都能理解,可惟独这一条令人失笑,人家既然还了俗,重新回到了俗世上,干么不录呀?顾山农答复说:这是明摆着的,如果他敢在上半天逃离佛陀和菩萨,解下袈裟,那么他一定就能在下半天踢开承平堡,更换门庭,这样的朝秦暮楚之辈,我不开这个口子。廖逢节也问说:咱们吃的是贸易这碗饭,讲求的是勤进快出,赚取利润,这嘴上殷勤的人,天生带有一种优良的本领,讨人欢喜,却又为何被革除在外了呀?顾山农斥责道:你个糊涂匠,你听着,承平堡既不需要喜鹊,也不招募老鸹,最好都是哑巴汉子,手脚灵便就可以了。当着入门不久的张汲水的面,管家被责难了一顿,忙红着脸说:也对,口敞之人把不住门,守不住秘密,我将来就是承平堡的一只看门狗,谁要是敢造次,我第一个咬掉他的毬。旁侧里,张汲水坏笑了一声。
筛选到了最后,名册里剩下了六十七人,顾山农全部圈定后,予以雇用,并提前发放了一个季度的薪酬,让大家交给各自的亲属,而后回来就位,抓紧准备开张迎客。伙计们兴奋极了,扑棱棱地拔脚散去,仿佛天空中南下的候鸟一般,将赞美和大拇指传遍了整个凉州,惹得街坊邻舍们艳羡不已。一时间,不惟凉州本地,甚至河西全境的目光,也都齐刷刷地瞥将而来,投射在了承平堡的身上,探问究竟。不过,另一则消息也随即追撵了过来,承平堡竟然搬动了郡老们的那个神仙班子,另外还邀约了城内外的一帮子士绅耆老,打算在重阳节的这一日,去城东的沙山上饮茶,且美其名曰:塞外一席茶。天呐,喝的是什么甘露汤,饮的是什么天河水,还需要那么劳神费力,跑到沙山上去炫耀么?啊啧啧,少东主顾山农的面子,真是比天还大,比地还广,他虽然辞掉了郡老的那个显赫位子,但显然,他才是议事班子的主心骨,拿事的当家人,另外的神仙们也只能惟其马首是瞻。毕竟路途太远了,走一趟实在艰辛,否则的话,武威城里的人们,一定会站满沙山,亲眼瞭一瞭这个茶咋喝,这个戏咋唱,同时一睹少东主的风采,也好给此后的余生,储备一些扎实而稀罕的谈资。
招募工作结束后,廖逢节和张汲水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本来,管家的身份,让廖逢节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管着承平堡的大小事务,说一不二。岂料,一个北疆来的恶汉子游击,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像一条疯狗似的,打算抢班,准备夺权了。这使得廖逢节昼夜惊魂,倍加小心,简直连大声咳嗽一下也不敢,天天提悬了心脏,阴沉着鼻脸。六十七名伙计被录用后,廖逢节看人下菜,并取得了少东主的首肯,将大家分配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同时,廖逢节还专门请来了城里最有名的挽具匠、修车匠、赶车匠,以及骡马师傅和草料师傅,手把手地传授技艺,让大家迅速上了道,技成出徒。廖逢节的一只眼睛跟着伙计们,另一只眼睛却盯住了那个游击,发现张汲水有事没事,总爱盘桓在少东主的身边,表情献媚,老鸹一般地聒噪不休。日能的,看把你日能的,明显就是一个舔沟子的货色么,廖逢节由此断定,并在心里渐渐地拉开了距离,事先防备了一手。承平堡太大了,堪比一座城池,安全问题尤为重要。顾山农从录用的人员中,划拨出了十几名精壮汉子,也未曾与管家合计,一发交给了张汲水,成立了护卫班。获知此事后,廖逢节差一点儿吐血,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除了精神上的不痛快,除了暗中使绊子,对护卫班申请的一些器械拖宕不办之外,他终究也是无计可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可耻的游击另辟天地,慢慢地做大,几乎快跟自己平起平坐了。有一日,廖逢节实在气不过,偷偷地去买醉,三更天才摸回了权家,蹲在前院的廊檐下唉声叹气,眼泪兮兮的。不料想,这一幕被小少爷窥见了,惊白喊醒了丫鬟,煮了一碗醒酒汤,赶紧端给了管家。廖逢节捧住汤碗,忽然间心魂归了位,知道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自己在权家的那一席之地,尚未被撼动,亦不曾被褫夺。闲谈中,廖逢节试探地问,究竟是管家的权大,还是一个护卫班的班头说了算?惊白简直不是人,他一定是从天上下凡的鬼精灵,加之耳食了姐姐平素里的一些絮叨,当即明白了对方之所以苦闷的根由。惊白开示道:哎呀,你心里的这个疙瘩,其实就像一碗水那么简单,那么明白,管家何许人也,管家乃是当朝的宰相,一手遮天的大人物,满朝的文武大臣,还不是看你的脸色行事么?班头算个屁,说得好听一点儿,不过是九门提督,往难听里说的话,顶多就是一条看门的头狗,你大可不必去计较。廖逢节顿生喜悦,泼掉了手中的汤水,追问再三,自己该如何应对。惊白张开了五指,又狠狠地攥紧了,攥成了拳头,款款地送出了一句话:一旦相权旁落,这个戏就唱不下去了,还得廷杖你,仔细你的屁股蛋子吧。相权旁落,管家反复咂摸着这句话,一直熬到了天明。待城门开启之后,廖逢节徒步出城,不动声色地回到了承平堡,仿佛去收复失地似的,心里头逐渐地有了一块钢。
岂料,张汲水可并不消停,效仿了新城大营国民革命军的方式,将护卫班的那十几个杂碎,天天带出了堡子,站在东北角的一块郊田上,开始出操,开始做戏。早中晚三次,一俟新城里的军号吹响后,张汲水俨然成了一只头狗,一手吹着皮哨子,另一只手挥着鞭子,勒令护卫们走正步,喊口号,摔跤,打拳,格斗,好像他本人开了一家凉州武馆似的,嚣张不已。后来,郊田上又多了一些石锁、石磨和拔河用的长绳,号称他们在练肌肉,长力气,乱作一团。廖逢节偷窥过几次,望见护卫们踩踏起来的尘土,像一块黄色的云团,罩在了郊田一带,免不了嘀咕一番:看把你日能的,日能了你还能上天呀。不过,类似的嫉恨与负气,很快就消弭了,被一风吹净,廖逢节讶异地发现,每当堡子外面喊声震天、脑筋错乱时,少东主往往会站在角楼上,一边朝下观望,一边面呈喜色,暗中叫好。终于忍不住了,有一次吃早饭时,管家故意提起了这一茬,连毛带草地讥讽了一番,说承平堡是做贸易的,以挣钱为重,耍那些花把式有个屁用,再说了,承平堡又不是革命军的分号,也不是新城大营的校场,天天驴叫,财神爷闻听后,恐怕也会吓得尿裤子,倒不如实在一点儿,干些人事。顾山农却不苟同,反而称赞游击张汲水有手段,思想巧妙,原先那十几个面色蜡黄的菜瓜,经过他这一段的锤打,如今一个个筋骨旺盛,肝火炽烈,这恰恰是承平堡求之不得的。末了,少东主又讲了一席话,气得管家撂下了饭碗,干脆饿了一整天,惩罚了自己。顾山农当时声称,他守了三年的孝,浑身的骨骼都快锈死了,等抽了空,他也打算换上一套轻便的衣裳,跟护卫班一道站在郊田上,野蛮体魄,蓄养精神。这倒也罢了,可顾山农接下来的话,令管家心荆肉棘,大感江山失守,一切已不复从前。顾山农笑说:哎呀,依我看,我亲自率这个头,你也参加,带上你的那些账房、车夫、马夫和杂工,投在张汲水的门下,将来谁也不吃亏,谁都可以长上几两筋肉。廖逢节当即回绝了:哼,瓜子不能当饭吃,那些指屁吹灯的勾当,花拳绣腿的把戏,真还抵不上这一碗捞面,我手里一河滩的事情,我不能分心,更不能出错。结果,这个提议不了了之了,管家没去,顾山农也不曾出现在堡子外的队列中,好像在戈壁滩上扔石头,一切均无从捡起。
这种微妙的变化,让管家品咂到了一种清晰的分野,一种分庭抗礼的黑暗力量。同时,管家也恍惚地觉出,少东主心中的那一台天平,或许已经动摇了,有了别样的心思。千思万想,前后琢磨,廖逢节大概推算出了一幕未来的格局,不外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由他来操心承平堡的内部事务,而那个不知好歹的游击,则去担负看门护院的任务,犹在外围,绝不是根脉上的角色。这么一思想,廖逢节稍微宽释了许多,深感时日漫长,这一番博弈将是持久的课业,自己以后必须睁着眼睛睡觉了。可偏偏,张汲水又施出了一记空前的辣手,喜滋滋地跑到了顾山农的跟前,邀请他以东家的身份,抽空去给护卫班的伴当们训话,紧一紧螺丝。廖逢节刚巧在旁边,怒斥道:哼,保价局是干贸易的,倘若你们一心想扛枪吃粮,穿那一身丘八的皮,最好现在就去新城大营门口排队,承平堡的这个庙着实太小了,装不下你们的金身。张汲水辩解说:哎哟,你这是误会我了,我的本意是这,原先我当保商游击的时候,每一次驼队开拔之前,领房子总要训话,子丑寅卯地说上一通,替大家打气,给伴当们膏油,这个法子真的管用。这个关节上,廖逢节沮丧地发现,少东主的屁股,已经坐在了对方的凳子上。顾山农击掌道:对呀,这个设想巧妙,可以给大家收收心,将一大堆缠麻拧成一股绳子,力出一孔,依我看,不妨就叫讲习社吧,你尽快去落实。事实上,在凉州境内,乃至于整个河西走廊一线,自古而来,便有结社的风气。比如,在长路上昼夜奔波的大小商贾们,喜欢成立行人社,彼此扶持,互相照应。再比如,在城外务农的庄稼汉子们,往往依据时情与天象,喜欢成立青苗社、瓜果社、萝卜社和洋芋社,等等。结社亦称邑义,凡是入社的同人,在人格上一律平等,贵贱一般,都是手足兄弟。邑义之后,讲求的是遇厄则相扶,遇难则相救,一方有难,八方来助,甚至于割己从他,不生怀惜。这还没完,顾山农转而对管家说:也好,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干脆将堡子里的大小人头全部召集在一起,我一遍过,如此也省去了诸多的泼烦。管家的牙齿几乎快要咬碎了,但舌头一下子答应了下来,答应得很痛快。
开讲的当晚,承平堡的新旧伙计们,乌泱泱地坐在了干燥的郊田上,有的盘膝,有的抱腿,用一张张热脸,迎向了少东主。对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他们头一次面见东家,聆听传说中的顾山农训话。紧张之余,更多的则是一份激动,大家事先洗了澡,剃了头发,穿上了干净的罩衣。彼时,日头站在了敦煌的方向上,夕光从祁连山上泼洒下来,似乎给整个承平堡,镀上了一层金粉,烁烨光华,堪比一座佛家的赞堂。顾山农出现后,并没有引起一丝骚动,四下里悄静极了,好像掉下来一根针的话,也会飞沙走石,山奔水飞。伙计们吃惊地瞭见,少东主并不是那个想象中的三头六臂、顶天立地之人,他个子中上,体形略瘦,颊脸上挂着一种憔悴的笑容,或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吧。顾山农站定后,双拳一抱,冲着大家揖上一礼,竟然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胶轮车子上,跷起了二郎腿,毫无架子,亲切得就像自己家里的姑舅。哼哈二将跟着过来,张汲水支起了一张简易的几案,廖逢节摆上了茶壶和碗,而后分列左右。此后,顾山农开了腔,侃侃而谈,先是陈述了承平堡的大概构想,又剖析了保价局这一项新式的贸易内容,少不了擘画前景,提升众人的斗志。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待张汲水点完了护卫班的名录,廖逢节又逐个绍介了其他人员之后,顾山农居然过目成诵,记住了全部的名字,还一一对上了号。闻听自己的名字,竟然从少东主的唇齿间喊了出来,每个人的心中,刹那间潮起了一阵阵醉意,纷纷仰看着他,浑身的骨骼就像一头头豹子,蓄满了力量。或许,这就是千百年以来,民间社会中结社邑义的根本道理吧。
夕光隐退后,暮色苍劲,整个凉州披上了一件寒瑟的秋衣,开始入夜。顾山农的这一席谈话,显得山高水长,传音入密,仿佛一双刚强之手,攥住了一捧散沙,即将锻造出一块崭新的炼砖,形成一支独立的势力,去拓土,去开疆,进而写下一卷河西大地的重大悲剧。
临近结束时,顾山农突然瞭见,一匹快马疾驰而来,家里的伙计跳下了马鞍,神色像一位八百里急递的信使。相问之下,伙计方说,县长吕介侯于夜饭之际,派人给权家捎来了一张字条,约少东主紧急见面,有要事相商。大小姐不敢耽搁,所以派出了快马,另外还带来了一套干净的衣裳和鞋子。这突兀的邀约,令顾山农大感意外,原因只在于他跟吕介侯之间并无私谊,平素里也谈不上什么交往,仅仅在外父权爱棠活着的时候,双方有过不多的几次碰面罢了。
亥时。文庙西侧的儒学院。顾山农问清了地点和时间,一瞧天色,八成是来不及了,赶紧接住了伙计手中的缰绳,一跃而起,跳上了马背,迅疾消失在了湍急的夜色中。
文庙位于武威城东南一角,屋脊连绵,高树密布,号称“陇右学宫之冠”,一向是令人景仰的圣地。大约还有半里地时,顾山农不敢造次,赶紧下了马,牵拽着缰绳,深一脚浅一脚地碎跑着,唯恐失了礼数,见笑于人。这个时辰上,夜色就像一坨康熙年间留下来的旧墨,艰涩冥顽,难以化开。快马的鼻息和蹄声,或许惊扰了这个秋夜的宁静,左右两侧的树丛中,鸦雀惊飞,空气像一页一页被撕裂的草纸,豁刺豁刺的。凭着记忆,顾山农绕过了大成殿的正门,踅入了西侧的车道。突然间,脚下头掠过了一道白光,要么是狐狸,要么是黄鼠狼,闪进了草丛中。快马蓦地被惊吓了,沸腾地嘶叫着,还险些拽脱了缰绳,幸亏被顾山农一把拉住了,赶紧抚了抚鼻门,让其收回了心魂。
动静一大,儒学院的偏门开了,一盏明亮的方灯飘了出来,迎向了顾山农。呃,可是承平堡的少东主么?对方探问说。正是,在下顾山农,答复道。对方豁然地说:快跟我来吧,县长一直在盼着你,已经候了将近半个时辰了。顾山农却不急,将坐骑拴在了门端外的石头桩子上,解下来一只包袱,掏出了妻子预备的干净外套和鞋子,匆忙换上后,又戴上了一顶礼帽。相跟着那一盏灯笼,七兜八转的,很快就来到了儒学院的内庭。顾山农认得这里,知道左右两侧的祠堂,一座叫忠孝,另一座曰节义。
这一时,县长吕介侯也挑着一盏灯笼,从节义祠的门廊下奔了过来,神色寡薄,心事重重,右手摘下了礼帽,略一颔首,打过了招呼。顾山农同样还了礼,却忽然感觉不自在,借着灯光往身上一瞧,天呐,自己竟然穿着一件府绸的外套,样子泼喇喇的,不仅俗气与滑稽,衣裳还相当肥大,好像随时会滑脱下来,掉在地上,暴露了个人的不堪。达云一定是糊涂了,或者被县长的邀约冲昏了脑子,似乎觉得只有高档的料子,才能配得上这个场合。无奈之下,顾山农只有暗中耸起了肩胛,拔长了脖颈子,衣裳才勉强挺括起来,接近于武威城内一介少东家标准的外表。吕介侯歉然道:哎哟,劳苦少东主一路奔波,给吕某这个面子,感谢的话不讲了,留待以后吧。顾山农抱拳,释解道:阁下,山农一得到消息,即刻就从城外赶来听命了,路上稍一耽搁,结果多花了半个时辰,害得你苦等了。吕介侯者,直隶大兴人氏,此前在省城兰州任职,大概在五年前被外放到了河西首郡,一直孜孜矻矻,倾心于当地发展,官声甚佳。吕介侯摆了摆手,款笑说:呵呵,你千万别自责,一来到文庙,我的老毛病可就犯了,我这不是苦等,而是耗子掉在了油缸里,求之不得呀。这种毫无官腔的自嘲,随性的表情,令顾山农一下子松弛开来,用眼神询问了过去。吕介侯指着节义祠的门廊,接续道:喏,那一方方碑刻,上头可都是张芝、江琼、索靖和余阙等河西诸杰的法帖,我是天刚擦黑时进来的,到现在也还没看够呐。顾山农不免狐疑,在这么一个更深露重的秋夜,对方紧急召见自己,该不会是谈玄说法、舞文弄墨吧?况且,凉州境内的笔墨大家们多了去了,再怎么宽容,轮也轮不到他这个姓顾的头上。这一番疑难的情绪,被吕介侯及时地捕捉住了,他遂将手中的灯笼交给了随从,唤其离开。眼睁睁地,随从的两只手各挑着一只灯笼,簌簌地退出了院子,四下里的夜色迅速填埋了下来,一派满坑满谷的样子。
阒寂之后,吕介侯在黑暗中盯视着对方,感喟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此乃《项羽本纪》中的陈词,顾山农内心了然,却也听见了讽刺,忙抱拳一揖,不承想,府绸的外套竟然从右肩上滑脱了下来,狼狈至极:让阁下见笑了,刚才来得太仓促,乱头粗服,鸡皮蛙脸的,万望恕罪,恕罪。但是,这个话题依旧打不住,吕介侯像一个蹩脚的裁缝那样,喋喋地说:呃,看人下菜,量体裁衣,其实这世上的任何一桩事,大体上都有正反两面,一个叫里子,另一个则是面子,如此才能维系下去,否则就穿帮了。顾山农一头雾水,暗中抓住了臂弯里的衣裳,重新搭在了肩膀上,不是因为冷,而是为了体面,回道:哎哟,阁下天语纶音,这是在开示山农,我的大福报来了。吕介侯轻笑说:呵呵,武威县之于本人,就像你身上这一件华丽而肥大的外套,表面上看似光鲜,但里头的身子骨却是不堪忍受,磨折不已,令人萌生退意。这一刹,顾山农明白了对方的禅机,也当即料定,这一场深夜的谋面,堂堂的县长大人绝不是来诉苦的,他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肺腑,要向自己倾诉。一念至此,顾山农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匆匆解开了纽襻,除下了府绸的外套,随手扔了出去。不巧的是,衣裳挂在了一根树枝上,清瘦地摇曳着,仿佛现场的第三个人。
果然,吕介侯蓦地抬手,攀住了顾山农的胳膊,询问道:少东主,你听说过柯达么?你知道上海的先施公司么?顾山农怔住了,不明就里,一再摇头。吕介侯并不意外:呃,你不知道也罢,其实我也不大清楚,只不过事发之后,我才多方了解到,那一台照相机之类的东西,恰是这个牌子的。闻听照相机这个时髦的词,顾山农坦白地说:阁下,我见识过它,我在城里的冰鉴照相馆拍过肖像,还不止一次。吕介侯失笑地摇头:不,这根本是两回事,冰鉴的那个玩意儿像一头蠢笨的骡子,而我所说的这个机器,大小就像一只棉靴,可以挂在脖子上,四处漫游,随时拍照。顾山农哑默了下来,静待下文。这么着,吕介侯方才道出了内幕,仔细说:前些日子,从省城兰州来了一名要客,此君姓张,名翘楚,身份是上海滩的一支笔杆子,有名的国际观察家。他此番行走西疆,考察山河,在陕甘两省轰动一时,大小官员们无不以结交张观察为荣,尤其是咱们的省主席孙蔚如阁下,对此格外重视,不仅在兰州肃王府的拂云楼上设宴款待,还亲自陪同他,先后游览了黄河铁桥与五泉山名胜,可谓是风光无限。接获了省府的电令后,武威方面自然也不敢慢待,我专门筹组了一个接待班子,又是锣鼓,又是唢呐,在古浪峡口接上了他,还在黄羊镇逗留了一日,这才吹吹打打地送进了城里,安顿在了霍去病驿馆。顾山农虽然天天在承平堡内忙碌,但也耳食了这一段时间的热闹,附和道:听说,阁下还陪着客人,去了一趟青土湖,去了一趟天梯山,在隔壁的大成殿祭拜了孔圣人,又在城外的果园子里,摘了大半天的果子,最后才尽兴而归。吕介侯哀叹道:的确如此,张观察做客凉州的前期,评点江山,访贫问苦,甚至还蹭过几顿庄户人家的粗食淡饭,大呼过瘾,此君的身上,一无骄矜之气,二无跋扈之相,县府上下真是喜欢得不行,但是,目下这一切全被毁了,武威方面做下的成绩,也基本上枉费了,实在令人痛心呀。暗黑中,县长的口气带着焦虑、烦躁与不甘,突然他一跺脚,惊走了树上的几只松鼠。少东主,请问这人世上最快意的事是什么?吕介侯猛地抛出来一句问话。顾山农率直地说:嗯,晚生以为,一枝独秀,莫如万木成林,所以最快意的事情,当数人抬人,僧抬僧。吕介侯一边点头,一边苦笑地说:呵呵,现如今的局面,却是人坑人,僧埋僧,武威方面的这个脸丢大了,丢到上海滩和江南去了,唉,我悔不该将他安排在霍去病驿馆,这个名字不祥,这明显是在给张观察去病么。终于,在这一番疙里疙瘩的铺垫结束后,吕介侯相告说:丢了,张观察的照相机丢了,另外还丢了一只皮箱子,凉州的贼娃子们简直翻了天,吃下了豹子胆呀。顾山农渐渐恍然了,这才是深夜的主题,至为核心的要义。
诸位看官,这台照相机所带来的无穷后患,将要掀起的一幕幕血腥风暴,远非在文庙的这一场托付便可以解决,就此终止。实际上,它才刚刚开始萌芽,接着抽枝,将来的恶果一定会滚落在河西大地上,腐败成泥,溃烂为疮。此处按下不表。
少东主,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去帮我把它寻回来吧,照相机,还有那一只皮箱。吕介侯慷慨相托,腰身微躬,虚上一礼。顾山农头皮一麻,身上立时开了锅:阁下,晚生乃一介素人,一毫无补,百身莫赎,加之服丧了三年之久,对这世面上的事情暌违太深了,实在是难堪重任,还请你再三斟酌,千万不要耽搁了大事呀。或许,吕介侯料到了这一种拒绝,轻笑说:唉,少东主总不会因为我孤家寡人,而跟那些势利的团伙一个样,不肯援手,站在一旁看我的可笑吧?顾山农忙释解道:阁下,俗话说车走车路,马走马道,像这样麻缠的案子,本应该是警察局的陈垦丁、张彝和王伯鱼的分内事,晚生只是一个买卖人,如此头大身子小的事情,我这辆车拉不了,也拉不动。呵呵,吕介侯灰败地笑开了,俯身捡起了一片落叶,慢慢撕扯着,掩饰住了尴尬:不错,这件事本来归陈垦丁,也归马警队和步警队去负责,去侦缉,但是这毕竟是一桩重大丑闻,如果事先喧哗出去的话,凉州岂不是弄得国人皆知,省府被动,赢得骂声一片么?哼,再说了,即便交给了警察局,那一帮热衷于窝里斗的家伙,也未必能让人遂愿,恐怕还会错失良机,永远也寻获不得了。阒寂中,吕介侯的手里传来了筋脉断裂的声音,那片落叶被撕碎后,扔在了脚下。这一刹,顾山农分明看见了县府和警察局之间,那一种巨大的隔阂与鸿沟,也获悉了吕介侯与陈垦丁二人之间的不睦。冥冥中,这个发现犹如一灯破夜,烛照在了顾山农的心中,并且对于承平堡未来的生涯,似乎有了一种天然的利好消息。顾山农咂摸着对方的情绪,盘算着进退的得失,态度渐渐地松动了下来,潮起了一试身手的念头。不料想,吕介侯却道:唉,看来我今晚夕碰了壁,撞上了南墙,只得无功而返了,少东主,你一定记住,咱们从没谋过面,刚才的那些闲章不作数,一风吹净了吧。言毕,吕介侯掉头走了,儒学院里一下子空荒了许多。
但顾山农终究是一介热肝辣胆之人,不忍对方失望,一个蹦子追撵了上去,在偏门下拦住了吕介侯,哀恳道:阁下,你刚才的托付,山农照办就是了,至于能不能寻获,全凭天老爷的意思吧,我心里着实也没个把握。吕介侯得到了答案,面色也挺括了不少,揶揄地说:哎哟,少东主手段神妙,连承平堡都可以起死复生,保价局也开张在即,只有你想不到的,却没有你做不到的,我现在放宽了心,今晚夕能睡个好觉了。这种叵测的话,令顾山农心荆肉棘,一时间无从应对,遂堆笑道:阁下,保价局不过是一只新饭钵,家中的几十口子人还指望着它呢,将来成与不成,也还是两说,况且阁下当初在保价局的相关文书上签了字,准予开业,鼓励贸易,又来函策励了晚生一番,殷切之情,山农自然铭记于心,没齿不忘。吕介侯踱开了几步,从旁边的树枝上,取下来那一件府绸的外套,吹了吹灰,仔细地递给了对方:夜深了,小心着凉,你赶紧穿上吧。顾山农接住后,将衣裳搭在了臂弯里,身上的那一口锅依旧滚沸,汗下如浆。吕介侯瞟了一眼,接续道:呵呵,衣裳不过是人的一个面子,就像承平堡是你的面子,保价局同样也是你的面子,但愿少东主将来有独立之思考,自由之魂魄,这一生只做你自己的里子,而不要为他人所役所屈,沦为一介傀儡,甘当幕后人物的面子。如此诘屈难测的话,仿佛一把撒出去的银针,迎面袭向了顾山农,让他的心中咯噔一下,眼底里几乎黑透了,一时间失语。临走前,吕介侯摸出来一封信,叮嘱对方抓紧去一趟霍去病驿馆,秘密行事,千万不要声张。待顾山农自夜色中回过了神后,儒学院里已经是死寂一片,惟有萧瑟的秋风,以及几只夜鸟陪伴着他,以防他心弦崩裂,精神错乱,找不见回家的路。
或许,这只是吕介侯的一次试探,一幕委婉的警告,一种敲山震虎的把戏。顾山农颓坐在地上,逐渐醒悟了过来,这才发现,那一件府绸的外套已经被他彻底撕碎了,手指头也疼得钻心。直到偏门外的坐骑开始嘶叫时,顾山农这才抬起了屁股,趔趄地出了门。
(节选自2022年第6期《芙蓉》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第二卷)》)

叶舟,诗人,小说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甘肃省作协主席。著有《敦煌本纪》《边疆诗》《叶舟诗选》《引舟如叶》《丝绸之路》《月光照耀甘肃省》《漫唱》《西北纪》《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秦尼巴克》《诗般若》《所有的上帝长羽毛》《汝今能持否》《大地醍醐》等30余部诗文集。作品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