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王海雪:莫比乌斯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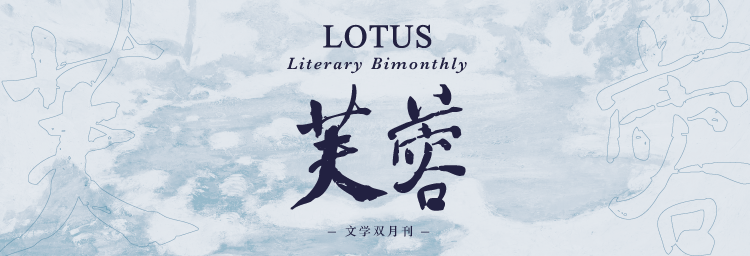

莫比乌斯环
文/王海雪
1
E星的命名简单粗暴,第一个抵达之人的姓氏首字母是E,因此,这个原本遥远而无名的星球便约定俗成地成为人类口中的E星。人类输掉那场最重要的战役之后,便走上各种层出不穷的星际逃亡路线。蛇头开出的价码几乎一日一变,仍然供不应求。飞往E星是宇宙最热门的航线,飞行成本低。E星又以乌托邦国的别名活在传闻里——一个虽然生活艰苦却没有战争存在的星球。
几乎人人买的都是单程票,虽然氧气稀薄,却能让人类有喘息的机会。杀戮依然在地球上秘密进行,地球联盟战线的暗杀小队四处活动,却也仅能杀死一些开始定居在宜居地带的异星平民——仿生体——这是人类对他们的称呼。
我离开那日,是一个阴蒙蒙的黄昏,我拎着黑色的手提箱——我全部的家当——登上了活动楼梯,没有回头,我最重要的人并未来送别,我不想看到那些无意义的生离死别的哭号场面。
只有头等舱才提供座位,大部分的人都紧挨着自己的行李,面无表情地或坐或蹲,来不及整理自己的七情六欲。战乱离散的痛苦在逃亡中不断褪色,活下来成为这一批人首要的目的,而我是其中之一。这场星际旅行的过程会是如何?听说可能会死,但是死法千奇百怪,人类对宇宙的想象是有限制的。
随着高度上升,我的眼前仿佛被亮光刺穿,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死了。但那仅仅是身体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做出的调整。
我抵达E星是早上,这里的计时和地球——现在应该被改为星都——完全不同。我注意到寒碜的广场上悬挂的两个长条计时历,一个是地球的时间,一个是E星的时间。也许E星的权威人士不想让人们把地球的一切忘记,所以时刻提醒人们地球的纪年。我并不喜欢这种愚蠢的行为,反抗当下才能得到未来。只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明哲保身,才逃难来到这里。
我暂租在一间铁皮盖成的活动板房里,这是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的人盖起来的。他们都是包机携带各种物资抵达这里,抢先一步占了地盘。这是一个自由而野蛮的星球,人们对从地球上照搬而来的法律并不认账,新的秩序还未在混乱中诞生,人们根本分不清杀戮和意外。我见过这一排屋子的末间住户,被人扔在了门口,手里还攥着钥匙。临时警察只是把他的尸体匆匆一裹,就运到牧场去了。牧场不仅饲养动物,也是一处极好的停尸房。无人知晓牧场的位置。如同乌托邦国活在地球人的传闻里,牧场则存在于E星的临时居民中。
人体腐烂的气味慢慢混入本就稀薄的氧气中,让呼吸变得更加奢侈,氧气的价格在黑市上水涨船高。我抬头看了半空中宛如一粒晶莹水珠的地方——玻璃城,那是一个例外。我使劲地嗅了嗅,觉得城中人应该闻不到这股难以形容的味道。
我的母亲没有来。她耗尽有价值的东西,给我买的票。
这是大部分老年人主动或被动的选择。E星无法装下所有人。于是,留在地球的,除了暗杀小队的人,便是老弱病残,亘古不变的道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适用。我经常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还好活着的,只有我母亲一个亲人,还好她自认为已经老到见惯了朝气与沧桑。她即将年满六十,决定把剩下的寿命给我。我有过加入地球联盟战线的念头,母亲却说,去E星,无论是死是活,都不要后悔为自己的决定赌一把。
我在板房里无事可做时,就会想她此刻正在做什么。地球上的普通家庭,几乎无法支付双人的票价,这或许是她固执要让我单独离开的原因。
人类没有什么好同情的,他们动物化的时候,比我们还残忍。这是获胜的仿生体宣布地球成为他们新的殖民基地后,在全球所有标志性建筑打出的一句话。那时候,人类还占据着地球的角角落落。可他们根本不担心会激怒地球人,也不担心暴动。他们有这宇宙最厉害的武器,不然为什么地球的抵抗会瞬间溃不成军?
2
每天一睁眼,如果不看向特制的床头时钟,我就分不清白天黑夜,这是从地球带来的仍然无法改变的习惯。在这永远黑暗的异星上,我还是用地球的作息来指挥身体内部的运转。来此后,我才清楚黑暗有深浅。我看向半空中的玻璃城,有人造的光,听说集中了地球曾经的达官显贵,就连他们所乘坐的传送带也是我所想象不出的高级。他们不会经历时间压缩身体的痛苦,也不会察觉空间变窄对身体的撕扯,而眼睛所能接触到的玻璃城泄漏的光线,是他们对我们的施舍。
到处是感激涕零的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不分种族,以自己的信仰起誓,对玻璃城里的首领表达自己的忠心。偶尔玻璃城会派人分发免费的粥,他们信奉的神祇指示他们这么做,那是深藏于宇宙深处的荒神,见过神的只有寥寥数人,所有关于玻璃城的神话都来自他们口中。人们说,他们是神的使者,是他们在玻璃城里建起巨大的神像,即使城内的所有光都灭了,神像的光芒却从未消减,这是先来的城外人跟我们这些后到者讲述的经历,在一次严重的电力中断下,神光是所有人的救赎。
我吃过一次免费粥,有地球熟悉的味道,却又加了这星球的佐料,有某种怪诞藏于其中,也许是这些食物经历了疲惫不堪的星际旅行。我抬头看玻璃城,边界之处有绿色的植物,和我身处的荒漠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注意到盯着外面的人,廉价的同情给早已斑斓的眼珠上色。那些居于顶端的人,从不愿意走入黑暗中,亲身体验在这个异星生活的艰难与痛苦。
我的邻居来自美洲大陆,丰厚干裂的嘴唇让他养成一个随时伸舌头的恶习,喜欢跟我讨论如何开荒扩大他的土豆地。地球即将灭亡,让种族歧视和所谓人权危机在国与国之间不复存在。因此,在E星上,这一排铁皮屋下,虽然时有龃龉,大家还算相安无事。
我把一小块土豆皮啃掉,吃里面的肉,他的土豆个子很小,吃起来干巴巴的,没有嚼劲。他说,你知足吧。然后,他抬头看天空中渺小的人影仰慕地说,她是玻璃城里的王。我惊诧于他良好的视力,转念一想又释然。即使玻璃城很坚固,但是困不住光,跑起来的光谁也追不上。一定是有光反射到他的双眸中。
我走到前面,继续抬头看那一丁点的光,我渴望看清那站立之人的五官,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邻居看出我的心思,他叫约翰,进屋取出一张画像递给我,说,长这样。我一边端详一边问他,你觉得美吗?他笑得污秽,女的就行。他是一个大概四十岁的单身汉,在这漫长无边的黑夜里,他首要满足的是自己的生理需求。我把那一张用铅笔绘出的画像还给他,明白这是他观察多日在自己脑海里描画的一张平淡的面孔。
人是多么狭隘又乐观的动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想到性欲,我不禁对约翰产生了可怜的敬意。他是墨西哥人,二十三年前,偷渡到邻国——美国——打工,在后厨炸薯条。不久,世界各处燃起战火,他和同乡挖了一个地下室,为了逃避可能的轰炸。虽然仿生体的武器可以钻入地下很深的地方,但是,人都需要一些安慰,而且挖地下室,能转移恐慌。你在这里也可以尝试做点事。他说。约翰从不放弃尝试。当他说到尝试时,总是浮现意味深长的笑。
3
能源紧张导致E星的电力供应非常不稳定,约翰带我去城外更偏远荒凉的地带买蜡烛以备不时之需。蜡烛的价格高得惊人。我犹豫着,跟约翰说,自己可以记住那些家具和瓶瓶罐罐的位置。我在约翰的帮助下开垦了一小片地,种上了番薯。这得益于母亲的先见之明。也许每一名母亲都担心远行的孩子忍饥挨饿,农活做得得心应手的她在我的行李里塞了一小袋番薯,正好让我拿来当种子。她还想把家里唯一制造精密的来复枪和所有的子弹装在里面,被我拒绝了。外面不时有流弹响过,不知谁生谁死。
我对E星并未有太多的想象,也没想过所要面临的艰苦条件,那些在地球流传的探险家的故事仅仅是让人们相信E星是一个好去处。不是这样的。我在心里孤独而大声地呐喊。是谁炮制了那些虚假的话,已经不重要了。约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个简单的人类共通的肢体交流,并未安慰到我。他接着说,反正回不去了。就让地球上的亲人有个希望吧。谎言也许就是在希望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的。他看了看天空,远处玻璃城的背部一片黑暗,他说跟巴比伦空中花园有点像也有点不像。我说你根本没见过巴比伦。
卖蜡烛的人不耐烦,吹灭了原本的一点火光,说,你们还买不买?我看不清对方的脸,说,四根。卖家打开了火机,接过了我支付的东西。不是货币,地球上的货币在此根本不通行。我给他的是一把小匕首,虽然我觉得交换不值得,约翰却说他知道有一处铁矿,正在秘密开发,以后这类东西不缺。所以,拿出去。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他说自己仔细研究过这里的土壤,矿物质是不缺的,但是食物危机可能会在以后出现,虽然现在已经很紧张,但还不至于争夺得鱼死网破,可我们要未雨绸缪。
我拿着蜡烛,在跌跌撞撞的黑暗中也不知走了多久,才回到铁皮屋,虽然约翰不断说他带了打火机,可以点一支照明,我始终不肯。约翰叫我杰克,他说我的鼻子很像他看过的一部神话电影里的主角,那个主角就叫杰克。他每次见我就喊杰克,而我心里想的却是露丝,那部伟大的爱情电影,每次我都会看玻璃城,仿佛里面的女王就是露丝——凯特·温斯莱特的化身。就像约翰对画像的憧憬,我的困惑暧昧不明,我喜欢的是电影里露丝的性格与美貌,还是凯特·温斯莱特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的角色?约翰说自己知道凯特的墓地,一些在地球活动的朋友是她的影迷,虽然墓碑已经被炸毁,但是影迷创造的暗号能让人们在她的忌日送上捧花。不过我不是她的粉丝。约翰说。
我躺到简陋的床上,不知是黑夜还是白天,虽然我开了灯,但是停电已经持续几天,我也不想浪费刚买来的蜡烛,便在这无边的漆黑里闭上了眼睛,即使在夜色里,睁眼与闭眼都是无效的,但身为人类肉体的局限性,还是要做做样子,抚慰一下。样子并未做太久。我感到肚子饿,便起来准备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粮食必须节约,为此,我已经减了饭量,只摄入保持基本身体所需的食物。我看到小窗外有白银般的光,这是抵达这里一个月后我第一次遇上这些温柔的光芒。约翰曾经跟我介绍,这是从另一个遥远星球照过来的圣光,这一天,是E星罪恶消失之时,因为光清洗了人们的恶念。我开门走出,看到不少人站在外面,仰望夜空,而玻璃城却一片死寂,为了让人们更敬仰这光。我想问约翰,那个有光的星球是不是也有地球人?那里的希望是不是更富足?
约翰看到我,绕过我,进屋把我还没弄好的薯片拿出来,一边吃一边说,这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白昼,所以没有人想在这天作恶。和地球上一样,白天的犯罪率比夜晚低很多。
每个月一次的光明,无人舍得睡觉。
4
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穿红衣的少年,大概十二三岁,看起来多日不洗的肮脏金发胡乱地落在肩膀上,两片单薄的嘴唇好像正喃喃自语。他手里拿着弹弓,朝天上射去,也许只是无聊的游戏,也许是为了把这难见的光打下来。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我走过去,问了他。他说他相信,往天上打的子弹一定会经过他父母家并落在他们的脚下。然后,他问我和走过来的约翰,我父母会死吗?
约翰突然气急败坏地说,不要幻想一切,要粉碎它,切断对地球所有的联想,因为我们现在是E星的新居民,我们要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也许圣光真的有魔力,让约翰说出这么漂亮而残忍的话。他的家人在他来到E星之前已经死于轰炸,那些关系疏远的亲戚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已经不再谋面,离开地球之前,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车祸现场的玻璃碎片。现在,他是这里最自由的人,这自由的容器里又都放满了空虚,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他看向被这光芒笼罩的空中之城,叹着气说对不起。他说的西班牙语,他情绪上来时就会说西班牙语,不管人们是否听懂。但是抱歉的话大家都明白了。
我喜欢约翰的一个原因是他还有愤怒。不知道是否待在暗无天日里久了,我觉得自己丧失了很多情绪,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愤怒对待一件事,我还怀疑我想念母亲时的心情是否正确,我不知该选择七情还是六欲作为想念一个人的标志。我既不感到痛楚,也不感到有任何的惋惜。我扫了一眼出来沐浴这柔光的人群,发现我和他们的脸色几乎都一模一样——像打了肉毒杆菌。
我问少年借了弹弓,弯腰捡起一个小石块,往玻璃城射去。我不清楚为何要对准它,也许是想把一角打碎,钻进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稀世珍宝,或者一睹神的尊容。约翰说,打不中的,而且……他环顾四周后才悄然说,有密探。
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是衣衫褴褛的普罗大众,那些乘坐头等舱而来的人不过是把E星当作他们的中转站。那些看起来富有的地方都有他们雇佣的代理人,不需要自己动手。我不相信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还会有人告密。约翰说,你以为人是怎么死的?仅仅是争夺氧气吗?他暗示我有人类叛徒充当仿生体的密探。我想起那些透明的瓶子在黑市上出售。人们无法辨别真假,因为不会开罐验真,把鼻子埋入的一刹那,氧气就进入体内。如果感觉不到畅快,那么就只是一个空瓶子而已,只能自认倒霉。所谓的秩序不过是一种蒙骗眼睛的表象。我和约翰都未买过瓶装的氧气,我们对活着也没有很强烈的渴望。
约翰把手上不多的薯片分了一些给少年。少年很快就吃完,骨瘦如柴的他住在和我们相反的街区,一片被建得更早的地方。据说是玻璃城里的人做的慈善,提供免费住房给正在发育期的少年,并在每间房里都放了讲述科学的课本,以供这些被迫中断学业的孩子能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吸收知识。少年说他的房间里还有一本讲述仿生体来历和如何侵略地球的小册子,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也许是想让他这一代能够更多地了解侵略者的罪恶,了解他们是如何摧毁我们美丽的星球的。少年接着说他从不记得地球美过,到处都是生锈的断壁残垣,到处是被烧毁的森林遗迹,到处弥漫着焦土的气味,所以,虽然E星氧气不足,对少年来说却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身体已经承受过惊慌、恐惧、血腥与暴力,仅仅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轻微头晕,他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这些书,只是为了在少年的脑海里种下单薄的理想。少年指着玻璃城,说,对准它。那里是玻璃城的尾部,我看不出那里有什么稀奇之处。可我还是照做。不足的力量并未让石块飞出很远。少年走过去捡回来。
约翰想着那些印刷粗糙的书,叫少年不要看,说看了以后仿生体就会在理想收获的季节,开着收割机而来。我们不是仿生体,我们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对这些垃圾般的理想做什么。
少年似懂非懂,觉得约翰不是太坏,约翰拿东西给他吃了,不是吗?他点头说自己也没有时间看,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弄吃的。粮食短缺现象初露苗头,对少年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吃的问题,而不是学习。
我们站在外面,看着光慢慢地从E星寸寸撤离。
5
这个星球上零散的建筑都不高,虽然开始有了一些娱乐,但人们兴趣都不大,一些有点生意头脑的人都琢磨着开辟新的商业线,经常聚在一起说话,黑暗里能听见彼此的声音算是一种慰藉吧。从地球来的人莫名其妙锐减了很多,听说以E星为基地,组织抵抗的人都被精准移除了。无人问精准移除是什么意思,也许被炸死了,或是被传送到专门关押人类的地球牧场去,据说每一个在那里的人都成了行尸走肉。其间,如今的地球统治者——仿生体——沿用地球的语言,却更换了许多词汇的意思:牧场代替了监狱,移除代替了失踪或者死亡。
这是以卵击石,只有傻掉的人才会这么做。他们中的一个嘲弄着地球上抵抗的人,谈论着这个星球上的资源,想着是否可以跟统治地球的新主人——仿生体——做生意。他们确信E星混入了仿生体。
正在看我和少年制作弹弓的约翰,突然走过去,朝那人狠狠挥了一拳。少年护住了放在地上的蜡烛,他怕他们的争执与扭打会把火光弄灭。那人敌不过情绪高涨的约翰,他一边骂约翰疯了一边挣脱开约翰,跑入无边的更暗处,时至今日,E星让我对黑暗的了解比从前更深。
约翰还想追,我跳过去拉住了他。我们都不知道远处藏着什么人。一个月唯一的光亮来临时,我们都见过被曝光的尸体,就像被挖空内脏的动物尸骨,我们不知道他们因何而生,因何而死。人类在E星上,比在地球上还要脆弱。我想着抵抗的组织,想着仿生体,油然而生一种绝望,我来到这个黑暗的星球,难道就比在地球上躲躲藏藏好吗?我哭了起来。约翰也跟着哭了,少年拿着半成品的弹弓,抱着我们也哭了。然后,我们听到别处也开始有断断续续的哭声,接着,哭声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持续了很久……
初来乍到的慌张与隐约的憧憬被这里的萧条与不断滋生的问题冲淡后,我们已经逐渐接受了在此生存艰难的事实。
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还好,气温尚算暖和,并未有冻死人的事件发生。我开始每天举着弹弓往玻璃城离地面最近处的一角打去,我已经知道少年指的是哪块区域。少年教了我很多技巧。玩弹弓和照顾那片逐渐繁茂的番薯地成为我日常最重要的任务。
我和约翰有时会守在各自的地里,怕自己的收获被人顺手牵羊。我躺在外面裹在毯子里时,也会一直盯着一动不动的玻璃城。与它有关的一切迄今还是传说。那些披着长袍施粥的人一直是安静的,在整个过程中未发一语。虽然不喜其味,我还是又领过一两次。队伍逶迤,有焦灼不安的气氛。施粥的人每次都是不同的。我跟约翰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秘密基地运送着这些代表玻璃城权威的使者。无论在这群逃难者面前树立什么形象,他们都要被迫接受,不是吗?约翰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说,不要怀疑人家的善心,我们有粥吃,还活着,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但是,我的番薯和约翰的土豆成熟后,我们都没有再去。跟着我们的少年也经常在约翰的屋内打地铺。有时和我们一起,躺在地里,拿着黑市上买来的手枪,猎杀打算不劳而获的小偷。我的听觉敏锐度大有长进,即使相隔甚远,也能听到轻微的动静。
少年那些免费赠送的书也在缺光的时候——常年缺光——被带过来烧掉了,这些书唯一的功能就在于此。火苗燃烧得非常短暂,我们仨围住它,也没能延长半分。我们只能用力地嗅着灰烬的气味,幻想它能把这星球的黑暗稀释掉一些。
我们的身体和生物钟都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每个人都比刚来时更虚弱和消瘦。睡眠的紊乱对健康有影响。我感到自己在这片小田里劳动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在打弹弓的时候,我的精力却不知为何如此充沛。少年说是因为调动了所有的能量在弹弓上,朝着精准的目标射出去时,这股力量获得了最大增值。约翰没事时就会教少年一些数学知识,约翰在他的学生时代数学成绩最好。他们把那些书都剪掉,做一个又一个莫比乌斯环。少年有天分,说这个环万物始终,首尾相连。
打弹弓时,我的目光从未离开过玻璃城那个离地面最近的地方,它像海水下的暗礁,不注意无法发现。少年的手上都是满满当当的石块,我无须弯腰,只需要从他手上取过这些,发射出去。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让火箭发射升空的工程师。而这些跟地球上的石头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更像是某种未知的矿物。我右手的食指长出老茧。始终捧着石块的少年双手开始生出灼热感,他笑着说自己的手热得可以生火。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约翰说我也是。少年说你们跟我拿得一样多吗?约翰点开燃油所剩无几的打火机,蹲下看着凹凸不平的地面,想找出可供燃烧的物质。少年拿起一块扔到他的头上,嘲笑他异想天开,还不如潜进森林偷木柴。
E星的树林快被砍光,为了让本就稀薄的氧气持续供应,代表玻璃城内权力的小型部队已经把那里封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让人类公平地享受氧气。
约翰觉得森林像一片独立的战场,他的目光看向那里时如同撞上天然的屏障。也许森林被一个透明的罩子罩住,里面丰富的氧气只是玻璃城里的特供。他刚来E星时,就打算潜进去,中途却被那些负责施粥的使者拦截了。他不想为此丧命,就回到住处。也是那天起,他怀疑有告密者或奸细,他接受不时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活得谨小慎微。
6
少年终于搬来和约翰住在一起。他说他在某一次熟睡中,突如其来的大风把屋顶全部刮走了,虽然他和邻居们找了很久,也没能寻回那些铁皮屋顶。也许被人拖走了。这个星球上,除了人这个累赘,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卖不了钱就卖命。
还好,虽然经常刮大风,这里却几乎很少下雨。在我来到这里的一年中,我只见过一次很难形容的暴雨,即使下水道再好的地球城市也接不住那么多从天而下的雨水。但是,E星吸纳了所有的水分。当时我站在门口,望着地里,觉得收成都会因这场雨水而毁于一旦。虽然约翰已经叫我不要担心,说E星的底部是空心的,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这些雨,而且这一年一次的雨水足够我们不会渴死。这就是这个星球的奇妙之处,让人夹在生与死的边缘。悲观的会说这是半生不死。乐观的会说安排得刚刚好。我问约翰,那你呢?他抽了一口自己卷的烟,袅袅的烟雾随着他的话语散尽在半空中:我不知道我这个躯体活着有什么用处,也许我可以在这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发现它的奥秘,所以我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约翰的动手能力很强,翻越禁止线的糟糕经历让他对人生的一切有所恐慌,他保持健身的习惯,为随时可能的逃跑保存良好的体力,这是没钱看不上精神科医生的自救。他能发现E星上一些可食用的富有蛋白质却长相丑陋的昆虫。我却拒绝吃这些昆虫,也许我还没经历真正的饥饿,觉得这样的拒绝是在维护人的尊严。约翰说,尊严在玻璃城里。
他做了简单的过滤管,能够把水的部分杂质过滤掉。水喝起来有腥味。第一次喝让我觉得喝水居然这么费力。我害怕刚刚腐烂的尸骨碎屑都融入了水中。也许是紧张或者肠胃不适,我那天拉了好几次肚子。第二天,约翰帮我把水管接上并说,我们这里缺消毒的东西和药品。
少年过来的同时也拎来了一个急救药箱,说他那一排的同龄人人手一个,不过有些人的被偷了,有些人连同药箱一起被偷了。你们是好人。我相信你们。少年披散的金发让他的脸颊看起来亮晶晶的,眼珠像一颗罕见的蓝宝石。我问他眼睛怎么变色了?他说是跟我和约翰在一起有了光,但也有可能是来自E星看不见的辐射导致的变异。他抬起自己的手肘。我摸到一块骨头。他说,你干吗?我说,你不是让我摸摸看畸形到什么程度了吗?他说,你误会了,我只是给自己打气而已,蓝色的眼睛比以前更漂亮。
除了照料番薯地,其余的时间我都用在打弹弓上。少年也会站在旁边,他说我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他,迟早有一天,能命中目标。他指着玻璃城那遥远得几乎看不见的小角落,那是这座空中之城唯一的缺陷,离人类的视线太近。我弄不清楚玻璃城为什么会有设计上的瑕疵。对着那里看久了,我会觉得很不真实。世界简单无比,是人类绘出了它的七经八脉,让它复杂化。
打弹弓和种土豆番薯的日子,让我们仨适应这个黑暗而宁静的环境。黑暗卷走了部分的喧闹,也卷走了部分的人声。无论做什么都变得轻手轻脚。有时我甚至会产生幻觉,听得到打出去的石块落地的声响,仿佛是摇滚现场的轰炸。
7
被少年改良过的弹弓,射程大大增强,那被重新打磨的石块第一次与目标擦肩而过。少年并不沾沾自喜,而是说E星有很多奇怪而有用的物质,他只不过根据约翰所教的知识合成了一些。我和约翰惊讶他太过聪明的大脑。他自己挖出土豆,用清水洗过一遍,也不剥皮,边吃边看着我。他似乎患上了强迫症,总是不断地纠正我的动作和速度。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开始期盼一月一次从外星球而来的光芒,我日日计算异星的轨道,突然很怀念地球。我问约翰是做一名狼狈的逃亡者好,还是在地球上持续以卵击石地抗争好?少年垂下双手,和我一样盯着约翰。约翰却正在想玻璃城的女王雕像,应付了事,说他也不知道。他专注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西班牙语。跟着他久了,我也懂了一些基本用语。少年学东西很快,已经完全可以用西班牙语和约翰交流。这时,我就在他们声音的伴随中,一次比一次更接近靶心——那个足够容纳下打磨得一样大小的石块的地方。
光来的时候,我几乎是二十四小时都朝着那里打。我陷入一种狂热中,急切地希望命中,急切地想知道命中后的结果。即使于黑暗中,我仍能准确知道方向,这也许是人类之所以能战胜其他物种的优势之一,我们有进化的能力。
番薯地的产量一直没有上来,而饥荒正在E星悄然蔓延,我们的守夜变得艰苦无比。地里发生了一次意外,少年顺着脚步声射出了子弹。第二天,我们看到篱笆外面五米远躺着一个死人。殷红的血迹被我手中的烛火照耀,我很久没去黑市地带,很久没看到这样明艳的颜色,内心居然有一种变态的激动。少年把人掰正,骑上去甩了几巴掌给那还没变硬的脸。然后跟我说,试试弹弓。那一刻,我像一个木偶人,把蜡烛放在平稳的地上,退回去,拉起弹弓把石头射出去,它穿过蜡烛的火光,落在死人的大腿上。
约翰说我们的游戏越来越残忍。游戏不会让人堕落,何况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成年人。少年边说边把石块递给我。他负责捡拾和打磨这些石块,他几乎整日整夜都在做这件事。约翰拿着自制的铲子把我们驱逐得离他远一些。他挖坑把人埋了。
我手头还有两粒近乎透明的石头,一头被少年磨得很尖,如果地球上最坚硬的是金刚石,那么我手上这个物质的硬度应该是金刚石的十倍以上。少年有一把不知从何而来的宝刀,只有那么一把刀,才能削出这些石头的形状。他说从前他住的那个街区,所有的少年人手一把,就跟急救箱一样。
我环绕四周,不知为何与少年年纪相仿的人都不上这里来。少年说,那里更舒适。接着,他指着玻璃城,说,这次你一定能射中。他的话给了我希望,这是我来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我和往常一样把手抬起,好像回到幼年之时,一旁的少年宛如庞然大物,操纵着我这个茫然无知的孩子。当我察觉到这种意识的错位时,“子弹”已经射了出去,像一道明亮的光线。我看到约翰闭了下眼睛,然后流下泪来,适应黑暗的眼睛承受不住光的刺激。
我听到巨大的风声,看到玻璃城内部闪烁巨大的火苗,应该是久违的火苗,把这个狭小拥挤的星球照亮,把稀薄的氧气烧光。我听到无数的尖叫,来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旺盛的火苗,而这火苗不是希望,而是要把我们的生存之地掠夺殆尽。
玻璃城像陨落的飞船,从天空落下来,所有人都惊骇地发现,被各种传闻包裹的玻璃城真身其实是一个巨型炸弹。巨大的响声和哭号声几乎要把这狭小的星球撕裂。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镜子反射的幻象,我看着这座空中之城土崩瓦解,在满面的尘灰中仰头倒下的瞬间,明白了这是仿生体对人类的一个实验,女王是假的,神也是假的,都是窃去人类文明的仿生体,试图打造另一个虚拟的人类社会,企图观察人类在异星上的行为与行动,也许,他们希望傀儡产生……就像他们在地球上打出的那行字那样。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兽性的部分就会跳出来,指挥着身体,互相残杀。我感到绝望正以血液为养料,慢慢生根,遍布体内。无论留在哪里,命运的齿轮已经给我们转好了位置;那些能够被说出的人类词汇,都包裹着我所无法抵达的无尽的历史。
各色传闻就是让人无法呼吸的薄膜,把人慢慢地缠绕至死。这是另外一个在异星的实验牧场。我看到少年站起来,在背后火光冲天的爆炸中,安然无恙……虽然灰尘四散,约翰还是喊出了他最后一句话:还没到最后,谁赢谁输不知道呢,记得莫比乌斯环吗?他倒下时的面无表情宛如默片时代的一帧电影画面。或许他早已明白了什么。
我断气之前看到了少年诡异的笑脸,也悟到一切,理解了约翰最后的遗言。
地球上的母亲一定比我活得长久,她有来复枪,以及地球联盟战线的战士。

王海雪,生于1987年,文学硕士。有作品发表于《钟山》《十月》《芙蓉》《长江文艺》《山花》等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漂流鱼》等。曾获海南省文学双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佳作奖、南海文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