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陈仓:不穿裙子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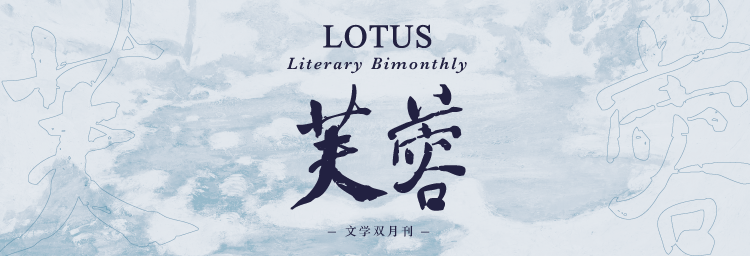

不穿裙子的女孩(中篇小说)
文/陈仓
1
人生就是一个盲盒,各种味道各种颜色都被随意地装在里边,在打开之前谁也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结果。在我的眼中,我的“初恋”余小卉,十二年前被装进盲盒的时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山区女孩,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偷同学的裙子被开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十二年后盲盒被打开的时候,像渔夫打开了魔瓶的盖子,她像一股青烟一样冒了出来,差一点惊掉了我的下巴——她竟然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成了一个裁缝,高级的称呼是服装设计师,而且设计的衣服进入了上海时装周。
2
那是2022年夏天的某个中午,我参加完上海时装周新闻发布会,正准备回报社写稿,《忘掉你像忘掉我》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生也猜不透,死也猜不透……这是我用王菲刚刚出道时唱的一首老歌设置的手机铃声。我瞄了一眼头顶的棉花云和毒辣的太阳,接起了这个陌生的电话,有些不耐烦地问:你是谁呀?对方说:你猜猜吧。我说:幼稚,懒得猜。对方说:你不猜我就挂了啊?!
那软软的不失深沉的声音,像刚刚吞下肚子的水晶粉丝,感觉十分熟悉又那么遥远。我试探地问:难道你是余小卉?余小卉说:谁是余小卉啊?我说:还能是谁,黑寡妇呀!余小卉说:黑寡妇死了,余小卉也死了,我现在的名字叫余顺兴。
天哪,余顺兴!这么一个老夫子一样的男性化的名字,怎么可能和当年的余小卉联系在一起呢?我猛然醒悟,难怪这么多年,余小卉离开陕西师范大学以后,像谜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更像在梦里曾经梦见的一个人一样虚幻,但是为之惋惜的感觉又那么真实。原来,她隐姓埋名,已经不叫余小卉,改叫余顺兴了。
我曾经向陕师大的学弟学妹们打听过余小卉的下落,有人说她回中学复读了一年又重新考上了大学,有人说她回农村种庄稼去了,有人说她给一个老板当了保姆,甚至说她长得像非洲人所以就嫁到非洲去了,也有人说在某某裁缝铺里遇到过和她长得特别像的女人。各种各样的猜测比较多,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余小卉似乎有点伤感地说:我以为你把我忘记了呢,原来你的狗耳朵还真灵,竟然听出了我的声音。我也感慨万千地说:是啊,仔细算下来,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我之所以听出了余小卉的声音,是因为她的口气和当年一样,像玫瑰一样暗暗地带着刺。不懂她的,听起来有些扎人;懂她的,便知道那是一种自嘲。
余小卉个子不高,下巴偏右的位置有一颗芝麻大的黑痣,因为经常帮着家里人干农活,皮肤被晒得黝黑光亮且十分细腻,身材不胖甚至偏瘦却显得比较结实矫健,让人感觉有着非洲美女的那种漂亮,再加上她平时喜欢穿着一身黑,我本来想给她起一个“黑玫瑰”的绰号,不知道为什么说出口的时候却变成了“黑寡妇”。
对于这个绰号,余小卉是抵触的,同时又是欢喜的。抵触的原因是“黑寡妇”听上去不像良家妇女,欢喜的原因是我答应过她,这个绰号绝不外传,天知,地知,她知,我知,只专供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用,类似一个心领神会的接头暗号。虽然我叫她黑寡妇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每次我叫起来的时候,她都会仰着头,停顿一下,显得十分享受似的看着我,像递过来一个黑芝麻烧饼似的,轻轻地答应一声— —唉!
就这么一声“唉”,像是轻轻的叹息,又像是发嗲撒娇,被她答应出了少有的韵味。不过,我叫她黑寡妇的机会不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最不是滋味的一次,也是十二年前的最后一次。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陕师大的校园云淡风轻,有一轮上弦月挂在天边,粉红色的樱花已经开了。我第二天将要离开陕师大,前往上海的《新闻午报》实习,有两个美女同学,一个是低我一级的学妹白苗苗,另一个就是余小卉,她们找了一个小饭店,点了几个小菜,还要了两瓶啤酒,非得为我送行。
吃完饭,喝完酒,又聊了聊天,然后大家就散了。谁知道,我刚刚回到宿舍,正准备收拾行李的时候,余小卉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发信息说有急事,让我赶紧下楼。我说:有事刚才怎么不说?余小卉说:刚刚不是有电灯泡白苗苗嘛。
我下了楼,问余小卉到底是什么急事。余小卉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就是有点舍不得你……余小卉说着,竟然伤感地哭了起来。我们两个就来到了昆明湖边,默默无语地绕着昆明湖散步,湖里有一对黑天鹅也在默默无语地游弋着。不知道转了几圈,夜已经深了,同学们都回宿舍休息了,我们便爬上了旁边的“不高山”。
陕师大长安校区属于新校区,本来是没有山的,是修建昆明湖的时候,用挖出来的泥土在西南角堆起了一座山。因为环境比较优美僻静,成了小情侣们的约会地,开始大家把它叫作情人坡,因为山不太高,后来就正式起了个名字叫不高山。山上种了桃花、杏花,最多的是樱花。山顶有一个环形的凉亭,早晚都有同学聚会于此,或者弹着吉他或者吹着口琴,抒发一点青春期的莫名忧伤。
现在已经是深夜,同学们早就散了,只有树林子里的小鸟,偶尔发出几声鸣叫。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余小卉突然一转身,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明白余小卉的心思,但是第二天就要启程前往那个陌生的城市,真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也有着对前途一片迷茫的担忧,实在是无法再增加一份感情的重量。我摸了一下她下巴上的黑痣,心痛地叫了一声“余小卉”,又叫了一声“黑寡妇”,她抬起头仰起脸闭着眼睛,十分期待地答应了一声“唉”的时候,我却把她从怀里轻轻地推开了,宛如无情地拂去一朵落在肩头的樱花。
不高山的不远处是篮球场,虽然已经熄灯了,显得黑漆漆的,但是仍然有一个人在打篮球,把孤独的篮球拍得嘭嘭直响。我们在凉亭坐了半天,余小卉才伤心地问:你到底嫌弃我什么呀?我就苦笑着告诉她,我不是嫌弃她,而是我喜欢穿裙子的女孩。我们村子没有一个穿裙子的女孩,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城里的女朋友,因为她们可以穿着花枝招展的裙子,像仙女一样在我的面前飘来飘去。
余小卉就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穿裙子吗?我说:因为你是农村的女孩呀。余小卉说:农村的女孩为什么不穿裙子呀?我说:裙子优点很多,通风,散热性强,行动自如,穿起来容易,样式变化多端而漂亮,但是你想想吧,我们农村的女孩,采药呀,种庄稼呀,打核桃呀,如果穿着裙子的话,上个山,下个地,爬个树,大腿甚至屁股都露在外边,到处都是刺,扎人不说,毛毛虫钻进去了怎么办?人家城里的女人就不一样,穿着裙子,上上班,逛逛街,跳跳舞,尤其是谈恋爱,亲热一下多方便啊!
余小卉有些生气地说:是不是像白苗苗穿的那样?!
白苗苗那天晚上穿着一条白色吊带裙,外边披了一件天蓝色的对襟毛衣,脚上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清新时尚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当时的余小卉,上身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外边穿了一件酒红色的夹克,拨浪鼓一样吊着几颗亮晶晶的大扣子,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大头皮鞋,上上下下捂得严严实实。我伸手拍了拍余小卉的肩膀,最后还加了一句:不穿裙子的女孩那还叫女孩吗?
余小卉听了我的话,目光像断电的灯泡子,尴尬地站了半天,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她的动作很慢很慢,解开一粒扣子像挪开一个磨盘一样吃力。她先脱掉上身的外套,再脱掉自己的牛仔裤,只留下了内裤和那件黑色的衬衫。
虽然已经是春末了,晚上的风还是有一些寒意,余小卉无所适从地站在风中瑟瑟发抖。淡淡的月光穿过樱花淡淡地洒在她裸露的大腿上,使得她像一根拔出一半的莲藕那么皎洁。我才突然发现,她的脸之所以那么黝黑,纯粹是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迷惑住了所有的人,而她的白或者叫美,却被捂在了深宫大院里。
余小卉缓缓地走了过来,再一次紧紧抱住了我,而且像一头麋鹿一样,用头在我的肩膀上蹭着。我一下子慌了,像木偶一样僵在原地,任凭余小卉像一个棉花糖一样融化在我的怀里。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她说:你不是觉得穿裙子方便吗?白苗苗穿着裙子,还需要你去脱呢,我自己脱光了给你,不是更方便了吗?!
余小卉再次提到白苗苗的时候,白苗苗还真就从夜色中冒了出来,双手插在裙子的口袋里,站在了我们的面前。白苗苗哈哈一笑,说:余小卉,你不知道吧?穿裙子之所以方便,那是因为连脱都不用脱……她提起裙子得意地旋转了一圈。
白苗苗的出现,把余小卉吓了一跳,她像兔子一样从我的怀里蹿了出去,哆哆嗦嗦地躲到樱花树的背后,十分生气地说:白苗苗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白苗苗从地上拾起余小卉的衣服,拿过去披在了她的身上,笑哈哈地说:对不起啊,我打扰了你们的好事。余小卉穿衣服的速度更慢了,她穿上的似乎不是衣服而是十分沉重的盔甲。
(节选自2023年第5期《芙蓉》中篇小说《不穿裙子的女孩》)

陈仓,原名陈元喜,1971年生于陕西丹凤县,现居上海。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著有“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八本,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小说集《地下三尺》《上海别录》《再见白素贞》,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诗集《诗上海》《艾的门》《醒神》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二届方志敏文学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