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冯积岐:没有说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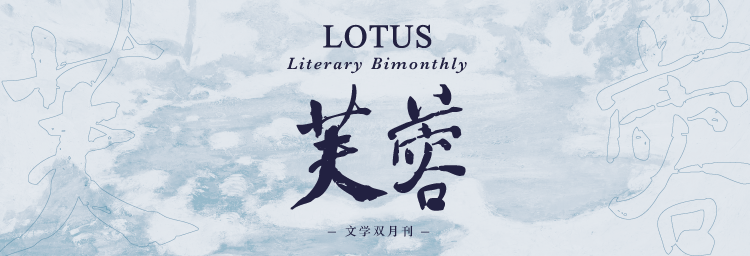

没有说出口(短篇小说)
文/冯积岐
现在,当我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已弄不清,居住在我头脑里的故事,有几成是虚构的,有几成是我把生活原盘端了出来——这很重要,如果我写出来的故事,有八九成是生活中原有的嘴脸,我很有可能犯了侵犯他人隐私的罪——况且,我讲述的是杀人案件(也有可能以污蔑人格罪被起诉了)。所以说,我是冒着坐在被告席上的大不韪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我总以为,我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可是,当事人不是我一个,假如当事人说,这是达诺写的小说,不是发生在凤山县的一个刑事案件,我就万幸了。
故事从黎明开始。
春天的黎明是软绵绵的——仿佛把手伸出去,手掌从雪白的、毛茸茸的一只小狗身上抚摸过去留下的感觉。也许,这个时候,年轻的情侣们依旧温柔地缠绕在一起,贪婪地爱抚着(因为是星期天)。我依傍着慵懒的春天,正在慵懒地酣睡(我有熬夜的习惯,感觉刚入睡),在通讯员十分坚定而小心翼翼的呼叫声中,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嘴里含着没有做完的睡梦的滋味问道:小张,什么事?小张说,达书记,公安局的李局长来找你。我必须说清楚,我是从省文联派到凤山县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这个星期天,我是值班的县委领导。李局长这么早来找我,必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我一脚蹬开了缠绵的倦意,下了床,用清水洗了洗脸,拉开门,到了办公室(宿办合一的套房,卧室之外就是办公室)。
坐在沙发上的李勇局长,一看我走出了卧室,站起来说,达书记,出事了。李勇那黑脸膛,一旦严肃了,就显得更冷峻。什么事?我示意李勇坐下来,李勇没有坐:杀人了。丈夫杀死了妻子,然后,丈夫自杀了。我问李勇: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李勇说,据推测,大约在凌晨两三点。我说,在哪里?李勇说,东大街的皇冠酒店。我把没有点火的那支烟放在了案桌上:走,咱去看看。
我坐李勇的车,出了县委大院。
昨夜下了一场小雨,湿润的空气里充满了泥土的香、花草的香、树木的香;香气清新而浓郁;星光褪尽的蓝天十分饱满,仿佛虚拟的天穹;清澈的空气流水一般触目可及。城市刚一苏醒,就不安分了,卖早餐的把节奏分明的叫卖声传得很远,很远——包子!豆花!醒目的空气中油条的味道、臭豆腐的味道、酸菜的味道以及茶水的味道,个性鲜明,不易混淆,相互竞争。生活的热闹和美好跟着黎明一起睁开了眼睛——也许,一刻也没入睡。生活永远那么清醒。行走在街道上,达诺即刻换了角色——他用一个作家的眼光在审度生活,而脱离了一个县委副书记的思维(也许是因为有一男一女在几个小时前离开了喧嚣的生活,离开了美好的人世间,达诺由此而感慨万端)。
皇冠酒店楼下拉起了警戒线。
我和李勇局长到了五楼——杀人现场,也是这夫妻两人的家。现场惨不忍睹。血腥味儿凛冽而顽固。妻子是丈夫一刀砍死的,那一刀,坚定而凶猛;刀中凝聚的能量和由此而释放出来的仇恨依然清晰可辨——女人的脖颈几乎被砍断,只连了一点皮肉。丈夫自缢在卫生间。刑侦人员告诉我,现场没有搏斗痕迹。女儿起来小解时,发现惨案已经发生,惊吓得半裸着跑下了楼。酒店的保安报了案。
丈夫为什么要砍死妻子,而后自杀呢?这是一部推理小说或悬疑小说的素材,达诺想,他如果是爱伦·坡或芥川龙之介,一部十分漂亮的、吸引读者眼球的小说将由此素材可惜的是,他没有虚构推理小说的能力。达诺在现场给李勇局长吩咐:按程序办,不要有疏漏。李勇局长自然知道什么是程序。
回到县委,达诺副书记给县委办公室的值班人员交代:通知各单位正职,上午九时,在县委会议室召开维稳工作紧急会议——挂职一年半的达诺,对于县委工作的程序已烂熟于心。坐在县委副书记这把椅子上的达诺,从这桩杀人案件中看到的是维稳,可是,作为作家的达诺,他必须换一种眼光去看这桩杀人案件,从这桩杀人案件中探寻人性的善与恶,探寻比善与恶更隐秘的东西。
既然我是虚构故事,不是照抄生活,我只能按我的思路讲述。这个故事中,丈夫名叫宋瑞祥,五十五岁;妻子叫金菊梅,三十二岁。金菊梅是凤山县皇冠酒店的总经理(法人代表)。
生活在凤山县城里的宋瑞祥和金菊梅,我是熟悉的。我好多次在皇冠酒店接待省、市、县(区)的领导和来访者。每逢宴请,金菊梅都要代表他们酒店来给客人敬一杯酒,一圈下来,客人每喝一杯,金菊梅要喝十杯。她喝酒的姿势不是很优美,但很有特点,容易被人记住——她用胖嘟嘟的三根手指头轻轻地把住酒杯,不是把酒杯放在嘴唇边向里吸,而是几乎把整个酒杯含进嘴里,向里倒——倒得很干脆,很潇洒——看得出,她对酒的轻蔑、无所谓和贪婪。我觉得,她不是强装的女汉子,确实有酒量,也豪爽。金菊梅高挑丰满——绝不臃肿,我之所以这样描述她,是因为她那翘得很高的两个乳房和隆起的双臂抢走的只能是丰满这两个字。一副标准的蛋形脸庞,可惜的是,额头太突出,一双黑漆漆的杏核眼下似乎遮出了阴影,使面部缺少了应有的阳光,而多了些阴郁——这只是我的感觉。她的笑容不是堆积在整个脸庞上,而是聚拢在目光里——她看人时,黑黑的眸子轻盈地一转动——用勾人魂魄形容可能最贴切。一旦她收回去笑,脸庞上的阴郁就遮掩不住了,目光里的孤独也暴露了出来。她染成浅栗色的头发浓密而蓬松,给她的漂亮增添了砝码。当她给客人敬酒时,裸露的半截胳膊白皙、丰腴而诱人,客人的目光不由得被这只胳膊牵走了。她浑身散发的浪漫而含有淫荡的气息像街道上漫流的污水,不可抗拒。而她的丈夫宋瑞祥,从不来这种场合,我见过他几次,他太普通了,普通得如同我们张眼就可目击到的沥青路面、楼房树木、商店餐馆。他的头发花白稀疏,脸上的皮肉松弛,眼皮耷拉着,脸庞上给人泄露的人生密码是疲惫不堪或年轻时的放荡不羁。金菊梅和宋瑞祥为什么会结成老夫少妻——当然在当今,这不是石破天惊的事(老夫少妻毕竟不是常态,也惹人注目)。我能感觉到,这两口子是有故事的。
如果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凤山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宋瑞祥,我喊一声老宋,他最礼貌的应答是,斜睨我一眼,头一扬,走了。凤山县城里的人齐刷刷地叫他宋总或宋经理,只有县委书记或县长一级的人物才叫他老宋。宋瑞祥有好几个头衔——凤凰家私有限公司总经理、凤山县家具协会会长、凤山县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凤山县政协委员。宋瑞祥的派头不是装出来的,好像与生俱来的一样,一身西装革履,皮鞋一尘不染——我仿佛能看见,他的女秘书蹲在他跟前给他擦皮鞋时那一丝不苟的样子。他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气派、气势,衬托得他周围的男人颜色暗淡。其实,他天生是个好演员,也许,搞实业是他的错误选择。假如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副县长或人大的副主任,他即刻换上一副笑脸——不,他的笑容好像迅疾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贴在了脸上。他拉住领导的手,十分亲热地握握,寒暄两句,匆匆别过,走出没多远,他就脸一沉,给随行的秘书说,十年前,他还是单位上的一个灶夫,当了个副县长,就人模人样了。他的副县长是怎么弄到手的,我清楚。假如迎面来了一个他想猎取的女人,他故意昂起头,目不斜视,一副对谁也不屑一顾的样子。等那女人叫他一声宋总,他面部的风景又柔和了——他的经验是面对想得到的女人,先要砍掉她身上的优越感和傲慢。他这样做,反而吸引了女人,这不能归于他有女人缘,这只是说,怎么对付女人,他是十分稔熟的。在生活这所大学里,他领到了一张文凭(尽管,他只是小学毕业)。
十五岁那年,宋瑞祥就混迹于社会——跟随表哥走南闯北,学做木工活儿。他由做家具改为只卖不做——在凤山县城开了一个店。生意是滚大的,名声是积累的。酒桌、牌桌、歌厅、舞场自然少不了宋瑞祥的身影——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是生活的常态,没有所谓的故事因素可开掘。即使他身边有几个女人,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感情纠葛——凡是能黏他的女人都比他年轻得多,这些女人能和他上床,同样,也可以和其他男人上床,哪里有那么多感情倾注给他——即使感情如同身体里的分泌物一样,这些女人的分泌物也是有限的。这些女人和他上床,还不是为了几个钱?彼此心知肚明,不挑明罢了。他的妻子对他的寻花问柳早有耳闻,女人并没有到公司来大哭大闹。女人的脸上常常挂着紧张与不安,女人发觉,她的丈夫好像没有和哪一个女人陷入感情的泥淖,她一厢情愿地把丈夫的宿花眠柳归结为玩一玩,归结为逢场作戏(说难听点,就像上了一次厕所)。久而久之,她也习惯了——这种习惯是可怕的——女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怕。夫妻表面上的和睦把夫妻间的矛盾和龌龊恰如其分地遮掩了。
故事在金菊梅出现之后开始了。
金菊梅是十六岁那年走进宋瑞祥和他的妻子金云云的生活的。
初中毕业,金菊梅没有考上高中,就去县城打工。那一年,金云云要生孩子了,她到娘家去,给哥哥说,叫侄女在月子里照顾她几天,哥哥满口答应了。金菊梅是以照顾姑姑的名义走进姑姑家里的。
在那一个月里,金菊梅对姑姑照顾得十分周到,由此,她博取了姑姑对她的偏爱。对于耐不住寂寞的宋瑞祥来说,女人的月子,更是他的狂欢节,他眠花宿柳,很少回家。况且,有金菊梅照顾女人,他十分放心。一月过后,金菊梅要回去,姑姑留住了她。于是,金菊梅就到了宋瑞祥的公司去上班。
金菊梅在公司办公室搞接待,来了客人或客户,金菊梅无非是给泡一杯茶,端一盘水果,或递一支烟。假如没有接待任务,金菊梅就跟着姑父的女秘书——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浑身每一根线条都具有诱惑男人的能量的女人——学习电脑打字。这个三十岁的女秘书,知道金菊梅是宋瑞祥老婆的侄女,因此在金菊梅面前褪去了有恃无恐的神情,做出亲热的样子来。在局外人的眼里,女秘书和金菊梅似乎相处得很融洽。
宋瑞祥在办公室出出进进,目光里似乎没有装金菊梅,而直接和他的女秘书对接,她被姑父忽略了——连达诺也估摸不出,宋瑞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这样做。十六七岁的金菊梅根本不在乎,一是她涉世不深,年龄小,对姑父和女秘书之间的故事没有心思去翻阅;二是因为姑父毕竟是长辈,她对姑父只有伦理上的尊敬和崇拜——姑父事业上的辉煌使很多人钦佩,当然也包括她。姑父的女秘书在姑父的休息室随便出入,在她看来,这是女秘书的工作,而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那个有点神秘的房间,是因为她的工作不需要。
故事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金菊梅来到公司的第二年夏天,有一天宋瑞祥在皇冠酒店(他已将这个酒店收购)接待广东的一个老板。那天晌午饭,宋瑞祥喝多了。是他的司机将他搀扶进休息室的——恰巧,宋瑞祥的女秘书回老家了,金菊梅值班。给宋瑞祥端水递茶的事就该金菊梅来做了。金菊梅第一次走进了姑父的休息室。她还没有来得及体味休息室的氛围,更没有来得及窥探暗藏在这休息室的秘密——她只是觉得这休息室宽大,幽幽暗暗的,有一股无法命名的味儿。她刚把一杯茶水递过去,站在床跟前,还没递到姑父手中,宋瑞祥一个翻身,吐了,污秽物和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喷洒在金菊梅的身上了。金菊梅说,姑父,要不要去医院?宋瑞祥摆摆手。于是,金菊梅开始清扫地板上的呕吐物,她去卫生间里打湿一条毛巾,给姑父擦脸、擦嘴、擦双手。在她给姑父擦洗的时候,姑父紧闭着双眼,呼吸好像停止了。金菊梅有了一丝莫名其妙的恐惧,突然,姑父将被她捉住手腕揩擦的那只手向上一伸,在她的脸蛋上摸了一下——金菊梅这才意识到,姑父是个活物,是个酒醉者。金菊梅的心跳加快了,她下意识地向后一退,张眼去看,姑父缩回去的手臂,灯光一样暗淡了。姑父闭上了双眼。当金菊梅清扫完房间,拖了地板,确认姑父已经熟睡之后,才脱下自己喷上好多污点的连衣裙,铺开在床上,用毛巾揩擦。这时候,姑父叫了一声:菊梅!金菊梅一愣,不知所措——是赶紧穿上裙子呢?还是赶紧和姑父搭话,她还在慌乱中,裙子刚提在手中,姑父又叫她。她说,姑父姑父,咋了?你没睡着?宋瑞祥翻身而起,示意金菊梅给他一杯水。金菊梅下意识地放下了裙子,急忙给姑父倒了一杯水,姑父在接水的同时,飞快地用蛇一样的目光在金菊梅半裸的身上扫了一遍,眼神一只蚊子似的在金菊梅小腹上叮了一下——金菊梅并未感觉到。宋瑞祥放下水杯,一只胳膊伸过来了,连金菊梅自己似乎也没想到,她竟然坐在了床沿,向姑父跟前偎了偎。宋瑞祥揽住金菊梅,一句话也不说。房间里灌满了两个人的呼吸。金菊梅脸红了,就这么偎依了一会儿。金菊梅感觉到,时间仿佛停滞了;停滞的时间就是一个炸药包;金菊梅忐忑不安地等待爆炸。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宋瑞祥说,我没事,你去休息吧。金菊梅长舒了一口气,这才穿上裙子,脸上的红晕还没有消退,她走出了房间。
金菊梅和宋瑞祥短暂的接触,刺激着达诺的想象,使他浮想联翩。虽然,金菊梅和宋瑞祥之间并未发生什么,可是,两个人的举动给达诺提供了足够的想象——故事的进展有了很大的空间。
面对一个成熟男人,面对一个长辈,本来,金菊梅应该羞涩、羞怯,甚至害怕——达诺这样揣摩金菊梅的心理。可是,少女被情窦初开迷住了——仿佛喝了迷魂汤——这使她早已渴望有一条强壮的胳膊揽住自己紧绷的皮肤,揽住跃跃欲试的肉体和不安的神经。金菊梅为什么没有拒绝姑父的搂抱呢?达诺只能按照金菊梅和宋瑞祥提供的行动线索讲述他的故事。
第二天,上了班,金菊梅随便出入姑父的休息室,这使宋瑞祥的女秘书觉得蹊跷而警惕起来,她并不知道,金菊梅和她的姑父之间发生的暗示——或者叫心理默契。这女人虽然被宋瑞祥宠着,却不能张口去问金菊梅:这是为什么?
宋瑞祥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出差,不再带他的女秘书,而是带着金菊梅。金菊梅每次回来都有收获——衣服、鞋、皮包,化妆品塞了一大皮箱。带着侄女出去开开眼界,金云云无可置疑——伦理在这个时候成了阻拦罪恶的金盾牌。宋瑞祥心里是明白的:正因为他带出去的是妻子的侄女,妻子才不会怀疑她——这比他带着女秘书放心——妻子肯定是这心理。聪明的金菊梅也没有忘记给姑姑带几件好衣服,以讨好她。达诺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写下去,结局会是什么呢?即使两个人做得天衣无缝,金云云终究会察觉的——尽管,不是捉奸在床,金云云也会有感觉的,她不会放过金菊梅投给宋瑞祥的媚眼,不会放过金菊梅在宋瑞祥跟前说话时超出伦理底线的语气——缺少对长辈的尊敬(甚至是命令的口气)。那么,结局无非是金云云大闹公司,或者抓破金菊梅的脸,或者抱着宋瑞祥不放;也许不是这样,金云云知道了宋瑞祥和金菊梅之间的奸情后不动声色地和宋瑞祥离了婚——家丑不可外扬。金云云的度量是能够吞咽苦涩的果子的,即使泔水她也会屏住气息喝下去的(毕竟金菊梅是她的侄女)。
然而,使金云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当她目睹金菊梅紧紧地搂抱着宋瑞祥的时候,她竟然放声大哭,而侄女却傲慢地说,宋瑞祥爱的是我,不是你,你看着办吧。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金云云已无立足之地——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扑进引渭渠中,漂到十几公里以外。这种悲剧结局,不只是金云云的选择,它符合金云云的性格。金云云既脆弱又刚毅。她看透了不说透,即使宋瑞祥和金菊梅明铺暗盖,她也装作不知道,她妄图给金菊梅和宋瑞祥都保住面子,给她的家族保住面子。当她觉得没有退路之时,只能选择这样的结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金姓人家措手不及,当然也包括金菊梅的父亲——金菊梅要和自己的姑父宋瑞祥结婚。昔日姑姑的姑爷要变为侄女的姑爷,妹夫要成为女婿——金菊梅的父亲勃然大怒:这不是乱伦吗?金菊梅振振有词:我和宋瑞祥没有血缘关系,就不算乱伦。我爱他,就要和他结婚。金菊梅的父亲只有一把撒手锏——和女儿断绝父女关系。金菊梅毫无惧色:不要说你和我断绝关系,你就是打死我,我也爱他,要嫁他。金菊梅心里只有宋瑞祥,她每天要和宋瑞祥在一起;晚上,只有被宋瑞祥搂着才能睡踏实。她才不管宋瑞祥是姑父、姨夫还是姐夫。她只是爱他,只知道爱他。
我爱他!
这种声嘶力竭的呐喊来自电视画面。我在S省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中看到,四川省一个1984年出生的女人,去河北省给她的姨夫打理网吧,爱上了姨夫——母亲妹妹的丈夫,两人非婚生子,母亲的妹妹被迫和丈夫离了婚。母亲教训女儿,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女儿尖声喊叫:我爱他!那喊叫声好像要把电视机喊碎。女儿哭着说,我爱他爱得要死,我们是真爱。你说怎么办?你总不能叫你的女儿去死。母亲很悲凉地说,孩子呀,那是罪孽,是乱伦。女儿说,我们没血缘关系。不要用什么伦理呀,道德呀为难我,这都是假的,只有爱是真的。这时候,主播用评论性的口气说,伦理,不只是血缘关系。伦,就是秩序。既然已有的秩序是父母辈关系,破坏了这种秩序就是乱伦。我们必须对挑战和威胁伦理、道德的行为发出声音,提出警告!固然,爱可以超越阶级、地位、民族、年龄;爱,同时是一个纯洁而纯粹的字眼;爱,不是一个包袱,把所有污脏的东西都能包裹了。主播的言辞再重,也砸不倒金菊梅这样的女人。
金云云去世还没有过周年,宋瑞祥和金菊梅就举办了婚礼。那一年,宋瑞祥45岁,金菊梅22岁。
宋瑞祥抱得美人归——和金菊梅在一起,自然要比和情人在一起,要比泡小姐放心得多,舒坦得多。在经营上,宋瑞祥松懈了许多,这恰好给了金菊梅插手的好机会。金菊梅先是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坐在了宋瑞祥的身旁,对公司里的业务指手画脚。宋瑞祥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出,这个漂亮的小女人是有野心的——她要的不是宋瑞祥,宋瑞祥毕竟人到中年了,能满足金菊梅的欲望吗?金菊梅压抑自己的欲望是为了把宋瑞祥的公司和财产弄到手。金菊梅步步紧逼。她一会儿甜言蜜语,一会儿恶意威胁,终于在爱的名义下,先是把县城里的三套房子的户主都换成了金菊梅,继而,把她负责的皇冠酒店的法人宋瑞祥换成了金菊梅。接着,她又对家私有限公司和一家宋瑞祥名下的超市打主意。宋瑞祥不是笨人,他已看出了金菊梅的企图,他觉得,金菊梅再翻腾,公司在他们一家人手里,不会易手——被外人掌控。金菊梅已和娘家人结下了仇,即使公司到了金菊梅名下,日后,还不是由他的子女来继承。不过,他还是要提防金菊梅的。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宋瑞祥四十九岁那年(和金菊梅结婚第四年),一场中风,宋瑞祥躺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宋瑞祥把几个公司全部交给了金菊梅。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公司。金菊梅也不必费心思变更法人了。金菊梅给宋瑞祥承诺,每年给他的卡上打十万元,由他支配——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宋瑞祥就充当了“太上皇”的角色。
第一年,宋瑞祥还有十万元花。他可以迈着僵硬的步子在凤山县城内外晃荡,或者坐在麻将馆,自由自在地打一会儿麻将。第二年,十万元变成了五万;第三年,五万元变成了一万。当年腰缠万贯的宋总只能借钱花。他去找金菊梅,保安拦住不叫他进金菊梅的办公室,他打电话,金菊梅不接。公司就是金菊梅的家,有时候,一个多月,宋瑞祥也见不到金菊梅。搬走了绊脚石的金菊梅天马行空,俯仰由她,不要说,她看中的小青年上过她的床,凤山县的很多达官显贵们和她一起纸醉金迷,也是生活常态;而她的固定情人是县政府的一位副县长,因此,她在凤山县城办任何事,都是一路绿灯。对于金菊梅的放纵,宋瑞祥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最明智的选择是装不知道。
宋瑞祥对放荡女人们的秉性摸得太清了——放荡是癌症,只有死亡才能制止它。因此,他只求安然无事。
最终将宋瑞祥激怒的是,他的颜面扫尽,没有一点儿尊严可言。他每天要抽烟,要服用降压药,要钱花,可是,他手中没钱,他看到了一个商机——皇冠酒店每天要消费上百瓶啤酒,和几十瓶白酒,他把那些酒瓶用三轮车推到收购站去,还可以卖几个钱,买一盒烟抽。头几次,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装上酒瓶,蹬上三轮,从酒店到收购站,一个小时之内,钱就到手了。那一次,他正在装酒瓶子,一个保安过来,喝令他把酒瓶子卸下,放回原处。他抬眼对保安一瞥,自顾自地装酒瓶子,保安拦住了他。他说,谁说这酒瓶子不能拉?保安说是金总经理吩咐的。他说,狗屁金总,她是我的婆娘,连她这酒店也是我的,我卖几个烂酒瓶子,还来拦我?保安一脸严肃:不行,说不行就不行。面对这个冷酷的年轻人,他毫无办法,他不得不把装进三轮车的酒瓶子一个一个卸下来,给人家堆放好。他满腹委屈,满腔怒火。他丢下三轮车,去找金菊梅。
金菊梅正好在办公室。两个保安拦他,没有拦住,他向里冲。也许,金菊梅早已料到宋瑞祥为什么来找他。金菊梅一看见宋瑞祥就说,你蹬上三轮满街跑,是给我扬恶名声,不是为了几个钱,我知道。再说,你卖破烂,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宋瑞祥说,你还知道丢人?人早丢光了,你算算,你在凤山县城黏了多少男人?从你床上爬起来的男人有多少,你记得清吗?你还知道丢人?金菊梅冷笑一声:我就是偷人来,养汉来,咱现在就去离婚,好吗?宋瑞祥知道,他和金菊梅离婚就意味着,他在人生场上输得精光,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公司,他的家。宋瑞祥说,离婚?便宜了你。老子做鬼,也要拖上你,不能便宜你。宋瑞祥用粗话骂了几句,走出去了。
金菊梅完全忽视了宋瑞祥的愤懑,忽视了宋瑞祥应有的自尊,忽视了宋瑞祥人性中那很恶的一面。她只看到了宋瑞祥对她的顺从、屈服以及无可奈何的处境,因此,当宋瑞祥挥动着寒光闪闪的砍刀之时,她依旧以为,宋瑞祥只是虚张声势,只是吓唬她;当砍刀猛地砍过来时,她才意识到,这不是游戏,这是人生,这是生命的绝境,可是,晚了,想躲也躲不及了。抬眼一看那寒光闪闪的砍刀,连我也惊慌得高叫一声:金菊梅,快跑!我这么一喊,金菊梅反而愣住了,站立在宋瑞祥面前——像一只挨宰的绵羊一样,等候那一刀——我依旧在我的故事中。
当达诺看到现场的惨景时,他的想象力飞驰:要么,这女人是在睡梦中被砍死的;要么,她误以为飞来的一刀不会伤害自己,只是一种恫吓;要么,她像罪犯一样,十分恐惧地等待惩罚,才使那罪恶的一刀砍得十分潇洒。可是,惩罚金菊梅的不应该是宋瑞祥。宋瑞祥是恶果的始作俑者。
故事中的金菊梅究竟是在什么状况下,被宋瑞祥砍杀的?这只能问金菊梅了,我把三种状况又重复了一遍,金菊梅坚定而忧伤地说,最后一种,等待惩罚。
宋瑞祥是怎么走进金菊梅的卧室的(宋瑞祥和金菊梅早已分开睡了,宋瑞祥住在皇冠酒店的五楼,金菊梅和女儿住在皇冠酒店的三楼)呢?宋瑞祥进去的时候就怀揣着一把刀,动了杀机?宋瑞祥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杀金菊梅?对于各种猜测和疑点,凤山县公安局经过侦查已经搞得清清楚楚,写进了案卷。公安局局长将侦查的结果告诉了达诺。
达诺在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宋瑞祥是在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左右进了金菊梅的房间的(酒店是宋瑞祥当时看着装修的,每个房间和防盗门上配有四把钥匙,他给自己各留了一把),宋瑞祥走进金菊梅的卧室的时候,金菊梅正在洗脚。她一看,面前站着的是宋瑞祥,不由得打了个颤,两眼呆呆的,嘴唇半张开,却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宋瑞祥是怎么进来的。于惊悚中,她横扫了宋瑞祥一眼,弯下腰,双手机械地在脚面上搓动,以此而掩饰她的慌乱。宋瑞祥开口了:给我些钱。金菊梅偷偷吁了一口气:他又是来要钱的,原来,他不是……金菊梅沉下了脸。她盯了宋瑞祥一眼:要多少?宋瑞祥嗫嗫嚅嚅的:要,要三百。金菊梅双眼挪回来,盯着她的洗脚盆。她说,好,你喝三口我的洗脚水,我给你三百。宋瑞祥迟疑了一瞬间,弯下腰,端起洗脚水,喝了三口。金菊梅一看,摇摇头,眼睛微微闭上,没有让泪水涌出来。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三百元,看也没看宋瑞祥,递给了他。
宋瑞祥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呕吐了,喷射状的呕吐,双肩抖动着,似乎要连同五脏六腑吐出来,当呕吐停下来,恶心如同滚滚的波浪平息后,宋瑞祥无比清醒。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爬起来,清理了自己的呕吐物。他睡不着了。深夜两点,宋瑞祥再次下了楼,走进了金菊梅的卧室,熟睡中的金菊梅没有来得及喊一声,就身首两处了。
我将写好的故事拿给李勇局长看。李勇说,达书记,你这是小说,我不懂小说,不敢乱说。凤山县的这个案子和你的小说不一样。噢?我长叹了一声。我不好过问案件的侦破情况——这是规定,也是纪律——只能给自己打圆场:生活不可能给作家提供现成的小说,如果是那样,人人都成为作家了。李勇吸了几口烟,半吞半吐地说,金菊梅有个相好的副县长……案情复杂了,现场有第三者的脚印。李勇把烟头狠狠地在烟灰缸中一摁,不再说什么了。我知道,有许多话他没有说出口,也不能说给我听。

冯积岐,陕西岐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50余篇,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遍地温柔》《重生》,散文集《人的证明》《没有留住的》等20余部。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柳青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