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冯俊科:乌蒙响杜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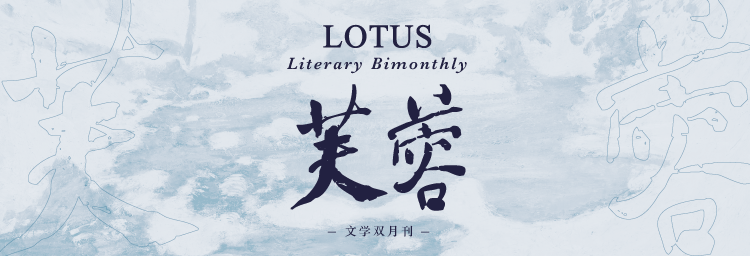

乌蒙响杜鹃(中篇小说)
文/冯俊科
军人的婚礼在军营里极其简单明了,尤其是在偏僻的乌蒙山区,在紧张繁忙的三线建设工地。
星期六晚上,新娘陈玉仙,新郎中队长龙岩炎,两张脸红扑扑的,像两人胸前戴着的大红花。指导员罗友军当司仪主持婚礼。首先,两人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面对面站着,准备互相鞠躬。谁知刚鞠了两个躬,突然有人在陈玉仙背后猛推了一把,陈玉仙一头扑在龙岩炎怀里。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
“还有一项没完呢。”罗指导员喊着,“给全中队官兵鞠躬啊!”
通信员借机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撒着喜糖,官兵们呼喊着去抢,像炸了窝的麻雀。老烟鬼八班长侯继天,身边聚着一帮小烟鬼,他觍着一张不怀好意的脸,点燃了一支金沙江牌香烟,抽了两口,故意用唾沫洇湿了半截,然后就硬往新娘陈玉仙嘴里塞。陈玉仙勉强吸了一口,呛得喀喀喀直咳嗽。二排长申国祥喜笑颜开,带着一群酒仙,端着茶杯、大碗,来到龙岩炎面前,乒乒乓乓一阵乱碰。龙岩炎毫不犹豫,把几乎满满一茶杯的山花牌散装白酒,一口气喝了进去。巫副中队长走过来,端着一碗酒,摁到龙岩炎的嘴边,龙岩炎挺直了脖子,央求着:
“老巫狗,缓缓,缓缓,老子刚刚进了一大茶杯。”
巫副中队长没有说话,脸上笑得很灿烂,他突然伸出强有力的胳膊,勒住了龙岩炎的脖子,硬是把那一碗酒,不由分说地灌进了龙岩炎的肚子里。现场非常热闹,官兵们嘴里嚼着大白兔奶糖,吞吐着烟雾,猜拳声此起彼伏,高兴得像是过年。听见啪啪啪响,有人在摔碗。原来是几个湖北兵,他们碰过碗酒一喝,把碗通通扔在地上,摔得粉碎。一个炊事兵心疼那些碗,指着他们骂:“中队长喝完酒是上婚床,又不是上战场,你们摔的哪门子碗?”
“谁说中队长不上战场?上啊!还要肉搏战呢!”
官兵们哈哈大笑。
“嗒——嗒——嘀嗒——嘀嗒——”,区队(该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建制,支队、大队、区队、中队,与师、团、营、连等同,排、班不变)部的熄灯号响了。
晕晕乎乎的龙岩炎,满脸通红的陈玉仙,被官兵们推推搡搡地塞进了新房—— 一顶搭在营房后面的绿色军用帐篷。
新婚之夜,新郎新娘激情涤荡过后,军用帐篷里变得寂静无声。大山深处的军营也是一片寂静。实在是太寂静了。“光棍儿好苦!光棍儿好苦!”突然有两只鸟,是杜鹃,它们不知从哪里飞来,丢下了几声鸣叫,又向哪儿夜游去了。这叫声真令人讨厌,骚扰得躺在大通铺上没有睡着觉的光棍汉们心里直发毛。龙岩炎有些清醒过来了。他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子,身材细长,嘴巴略大,眉毛粗黑,两个眼睛很大,平时总是瞪着,像一双牛眼,炯炯有神。现在的他半倚靠着床头,慢条斯理地吸着烟,那双牛眼半眯缝着,看着躺在身边的新婚妻子,像欣赏着一只猎获来的小兽,脸上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问:“玉仙,告诉我,为啥同意嫁给我?”
“我原不想嫁给你。”
“为啥?”
“我结过婚。”
“我知道,他早已死了。”
“那,也不想嫁给你。”
“到底为啥?”
“我在寻找一个人。”
“谁?”
“当兵的。”
“哪个部队?”
“不知道。”
“啥名?”
“不知道。”
“那你怎么找?”
“我知道他做过的事。”
“啥事?”
陈玉仙坐起身来,抑制不住激情过后的兴奋,把需要说的,一股脑儿地告诉了新婚丈夫。听了陈玉仙的诉说,龙岩炎不由得大吃一惊,牛眼瞪得溜圆,嘴唇哆嗦起来:
“这,这……怎么可能?”
“这咋就不可能?”陈玉仙吃惊地看着他。
第二天一大早,吕大山接到了龙岩炎的电话。他简直不敢相信龙岩炎说的是真话,他甚至不敢相信打电话来的是龙岩炎。
“你是龙岩炎?”
“龙岩炎。”
“结婚这么大的事,为啥不报告?”
“报告了,大队政治处批准同意的。”
“扯淡!我说的是为啥不给老子报告?”
“老猴子,上级有要求,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一切从简,除了本中队官兵外,其他中队,包括区队领导,一律不告诉,不邀请参加。”
“老子是其他中队、区队领导?”
“不扯别的了。现在我打电话告诉你的,不是我的婚礼,而是告诉你,五十年代初你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笑话!老子五十年代初犯下的错误,还严重,你那时在哪儿呢?你拍拍脑袋好好想想,是不是还被老子们的部队围困在县城里面呢?你这个国民党逃兵!哎,老子问你,你现在是不是还搂着你那新婚娇娘,没有睡醒啊?”
“老猴子,你听我说。”龙岩炎告诉吕大山,“当年你在这一带剿匪,是不是遇到过一个姑娘,十六七岁,对不对?这事你说过。你喝酒多了,说过,说过不下两次,对,应该是三次!我都记得。我妻子说的那人,好像就是你。那次你带领我们一中队,从鹰嘴峰去盘江镇执行任务,驻在凉透河的那天夜里,你黎明前失踪,干什么去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吕大山一下子哑口无言,半天没有出声。
“老猴子,说话啊?”
吕大山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发抖:“龙岩炎,你给我听好了,你小子先不要胡扯八道!你要是搞错了,小心我剥了你的皮。”
“你最好过来一趟,好当面验证清楚。”
一辆三轮摩托,风风火火地驶来猴场,驶进了407大队三区队一中队营区。骑摩托的是吕大山,402大队一区队长。他三十岁出头,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一身特意整理过的军装。他的脸面瘦削黝黑,双眼皮下的两只眼珠乌黑明亮,充满着精明和智慧。一看就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典型的训练有素的军人,精干利索,英气逼人。
吕大山和龙岩炎,来到营区后面的山坡上。一个坐在石头上,一个坐在草地上,看着那条喀斯特河谷,听着那二十多米深处喧嚣奔腾的达莎江。旁边不远,两棵杜鹃花已开了。这两棵杜鹃花,大概是背风朝阳,得益于天时地利,开得有些早,开得很鲜艳,像是被鲜血涂染了一样,格外耀眼。
“新郎官儿,知道这叫什么花吗?”
“问傻子呢?杜鹃花,也叫映山红,还叫山石榴。扯淡!”
“好!还算清醒。知道它为什么那么红,与啥有关?”
“老猴子,你到底想说啥?”龙岩炎有点儿急了,“说正题。”
“不知道了吧,新郎官儿?”吕大山有点儿故意,“据说它的红,与一种鸟,叫子规鸟有关。子规鸟也叫杜鹃。相传周朝末年,蜀地君主杜宇,因冤屈深重而死,化作了杜鹃鸟,它日日夜夜鸣冤啼叫,声音凄楚悲凉,以至口中滴血,染红了花朵,这就是杜鹃花。唐朝有个叫成彦雄的写道:‘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
“操,还没细说呢,就冤屈你了,还口吐鲜血?”
“别急,听我说。南宋的辛弃疾写:‘百紫千红过了春。杜鹃声苦不堪闻。’最著名的当数李白:‘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行了行了,别什么杜鹃花、子孙(规)鸟了。”龙岩炎单刀直入,挑开了两盒军用罐头,一盒猪肉的,一盒是鱼肉,“说说凉透河的事。”
吕大山微笑着,递给龙岩炎一根芦笙牌香烟,点上,自己也点上一根。两个老战友,一瓶三花牌白酒。吕大山谈起了十几年前的凉透河。
凉透河在乌蒙山区腹地,是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寨,居住着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七八个民族。凉透河的四面都是大山,进出只有一条道,也是唯一的通道,就是必须攀登一段天梯。那天梯30多度的斜坡,30多米长,很窄,很陡。上下天梯须手抓铁链,脚踩石窝,一步一停几步一歇,非常难行。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山崖,崴脚摔断腿是常有的事。寨子西北面有一座清风岭,常年云遮雾绕看不见峰顶。清风岭脚下有一个巨大山洞,一条暗河从山洞里流出来。河水冬暖夏凉,天气越是炎热,河水就越是冰冷。凉透河村寨,大概是因此而得名吧。河水经过寨子南面,从东南流向了一个叫飞龙峡的地方。飞龙峡两边是悬崖陡壁,没地方能够下脚,河道在峡谷中流了七八里,突然一下子跌落了下去,河水变成了大瀑布,飞流直下,水雾升腾,下面深不可测,啥也看不清楚了。河的南面有一个平坝,是这个寨子仅有的一块平坝,两亩多大,有一座庙。
连接寨子和庙宇的是一座桥。据说,这桥是清朝康熙年间,寨子里一个富人集资修建的。桥下由几块巨大石墩支撑,桥面铺着木板,两旁设置栏杆、长凳,顶部盖有瓦片,下面有廊式走道。桥头建有两个亭阁。行人走在桥上,因能躲避风雨,也叫风雨桥。这风雨桥,传说中起着“锁水”“拦龙”“护寨”作用,现实中是村民迎来送往、款待宾客唱“拦路歌”、喝“拦路酒”的场所。
“老猴子,能不能别再转弯抹角,说什么凉透河、飞龙峡、风雨桥啥的?”龙岩炎有些不耐烦,“说!说你当年犯下的错误。”
吕大山笑了笑,吐着浓烈的烟雾酒气,道出了自己当年在这风雨桥上,在这个寨子里,欠下的一桩无人知晓的情债。
五十年代初,吕大山在解放军418团三营当侦察排长。解放军145团、418团围歼了陈白莲大部匪徒后,吕大山独身一人,奉命到凉透河侦察女匪首陈白莲的行踪。这女土匪首陈白莲,双手打枪百发百中,飞山越涧如履平地,被称为女飞仙。在六盘江乃至整个乌蒙山区,可以说无人不知。陈白莲虽说不是凉透河人,但根据情报,陈白莲在凉透河有亲戚。吕大山过那段天梯时,天下着小雨,不慎崴伤了一只脚。傍晚时分,他拖着伤脚到了风雨桥上,再也走不了了。为防止意外,吕大山把手枪、弹匣,藏在桥头一个隐蔽地方。这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牵一头牛路过。姑娘发现了他,停了下来,伸出柔软富有弹性的手,拉着吕大山的手,把他扶了起来。吕大山猛地一疼站立不稳,一个趔趄将要摔倒,姑娘一把抱住了他。顺势,他也紧紧抱住了姑娘。这是吕大山有生以来,第一次亲密无间地接触了异性身体,浑身有触电般的感觉。这感觉,让他忘记了疼痛,忘记了害羞,也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姑娘落落大方,像对待自己亲人,把他推上了牛背,驮他到自己家里,藏在了自己住的阁楼上。姑娘告诉他,她叫陈玉仙,是苗族。吕大山对她,则隐瞒了自己身份,说:“我是遵义茅台镇人,卖酒的,从云南沾益卖酒回来,路过这里。”
当年的吕大山年轻英俊,一表人才,长着一张讨姑娘们喜欢的脸。陈玉仙父母发现了吕大山。陈玉仙告诉父母说,这是自己在“游方”时认识的,摔伤了腿,走不了了。
游方,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恋爱和追求异性的代名词,也叫耍姑娘、摇马郎、谈小伙,它是苗族一个古老的婚姻习俗。苗族村寨一般都有游方坪、游方坡,专供未婚青年男女一起对歌、吹芦笙、吹木叶,谈情说爱,寻找意中人。也有未婚青年男女单独游方的。往往是夜深人静时,女方家人都睡了,姑娘的门半开着,屋外站着心情急切满怀渴望的小伙子,屋里站着羞羞答答满脸红晕的姑娘,一人门里,一人门外,两人脉脉相望,绵绵蜜语,倾诉着爱慕之情。
吕大山和陈玉仙,没有经历过这个浪漫过程,吕大山是直接进了姑娘屋里,直接躺在了姑娘的床上。
陈玉仙父母纯朴厚道,相信了女儿的话,把吕大山当成了自己女儿寻找到的意中人,用苗药帮他敷治伤脚,好吃好喝,无微不至热心照顾他。
吕大山发现,陈玉仙长得非常漂亮。蚕眉凤目,皮肤白皙,仙女一样。头上挽着大髻,插着鲜花、木梳、银钗等头饰。耳朵上佩挂着白银耳坠,晃晃悠悠地闪烁着银光。脖子上套着银项圈,也一亮一亮的。她上身穿着蓝布无领大襟短衣,衣襟和袖口镶有精细的水云花草纹图案。下身穿青布百褶裙,长过膝盖。绣花裹腿。脚上穿着一双精巧结实的蓝布鞋。只是个子不高,看上去也有些瘦弱,有些单薄。就是这个陈玉仙,用一双姑娘的手,每天抱着吕大山那只摔伤的脚,用十根充满柔情的手指,翻来覆去帮他按摩揉搓。吕大山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激情飞扬的年纪。在这个宁静温馨的安乐窝里,一双姑娘饱含深情的手,按摩揉搓得他心旌摇动,不能自己。陈玉仙也是情窦初开,芳心浮动,爱意绵绵。两人干柴烈火卿卿我我,记不清哪个时辰,突然间烈火熊熊,男女之间的那道藩篱化作了灰烬。很快,吕大山的伤脚明显有了好转,可以自由行动了。一天晚上,后半夜,东山头升起了一轮明月。吕大山起床小解,发现一个人影,背着背篓,向房后面走去。吕大山觉得形迹可疑,悄悄跟了过去。屋后面是座柴草垛,柴草垛旁边是一座小柴屋。那黑影打开小柴屋门,把背篓递了进去。就在那一瞬间,借着明亮的月光,吕大山看见那黑影是陈玉仙的父亲。那小柴屋里,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啊,那是一张吕大山熟悉的脸,在侦察排时他认真看过她的照片。
黎明时分,吕大山不辞而别,悄然离开了凉透河。
第二天,也是晚上,天上没有月亮,地上夜色漆黑。吕大山带领T连,悄悄来到凉透河,在陈玉仙家小柴屋里,没费一枪一弹,抓获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女匪首陈白莲。
后来,吕大山随部队继续在乌蒙山区剿匪。当时贵州的土匪众多,匪情极其复杂,剿匪任务十分繁重。吕大山随部队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剿灭了“黔桂边区挺进军”总部及直属第二团,活捉了匪首屠占廷;将“戡乱建国军”总司令陈一鸣,“挺进军”四纵队参谋长击毙。总之,由于剿匪战事频繁,山高路险,地域偏僻,联系不便,吕大山再也没有回到过凉透河。西南剿匪结束后,吕大山随部队奉命入朝作战,回国后在铁道兵X师修筑铁路,一去又是多年。他和陈玉仙完全失去了联系。但是,吕大山一直惦念着陈玉仙,惦念着陈玉仙朴实厚道的父母。
1965年,吕大山在铁道兵第X师18团担任一营长。修筑贵昆铁路挖掘鹰嘴峰隧道期间,吕大山曾来过凉透河一次。他先是到了风雨桥。风雨桥头一间木房子是供销社,售货员是个姑娘,20多岁。姑娘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婀娜。吕大山进供销社,买了一盒芦笙牌香烟,掏出一根点上,把一大口烟雾吐了出来,问:“小妹,寨子里是不是有个叫陈玉仙的?”
“兵哥哥,有噻。”
“现在干啥?”
“你问她干个啷?”
“不干个啷。”
“哦,你是不是耍姑娘哟?”
“不是不是,顺便问问。”
耍姑娘这话,吕大山听着刺耳,脸上有些发烧。他赶紧摆了摆手,走出了供销社。吕大山对这个寨子大致上还熟悉,知道陈玉仙家的位置。当他找到陈玉仙家,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这里已经没了房舍,更没了人家。原先住过的房子、柴草垛,柴草垛旁边的小柴屋,全都没有了。看到的是房舍的残骸,歪七扭八的木板、梁架,几件破烂蓑衣,几个缺面断腿的凳子,两个没了底子的背篓,一把锈迹斑斑的头、犁铧等。斑斑点点的陈旧炭痕,显示出这里当年曾被一场大火烧过。废墟上,长着血红的杜鹃花,还有荒草、葵花和野藤等。
这种惨状,散发出一种凄凉气息。令吕大山感到非常意外,心里一阵发冷。
吕大山再次来凉透河,就是带领龙岩炎的一中队前往盘江镇。黎明前他悄悄起床,佯装去厕所,跑到了风雨桥头供销社。女售货员穿着睡衣,睡眼蒙眬地接待了他。女售货员认出了他,说兵哥哥上次您来过,找玉仙姐,耍姑娘,她早就不在这寨子了……
吕大山一脸悲伤,讲得如泣如诉。龙岩炎一脸惊异,听得如痴如醉。两个老战友,一对生死弟兄,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峡谷纵横人烟稀少的乌蒙山区,会面对着同一个女人。
在感情道路上,咋竟然会有这种奇遇?
(节选自2022年第6期《芙蓉》中篇小说《乌蒙响杜鹃》)

冯俊科,河南温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72年入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某部服役。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现任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当代》等刊发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疑兵》《尘灰满街》和《冯俊科中短篇小说集》《江河日月》等作品集。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阿拉伯语等在国外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