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向本贵:上垭下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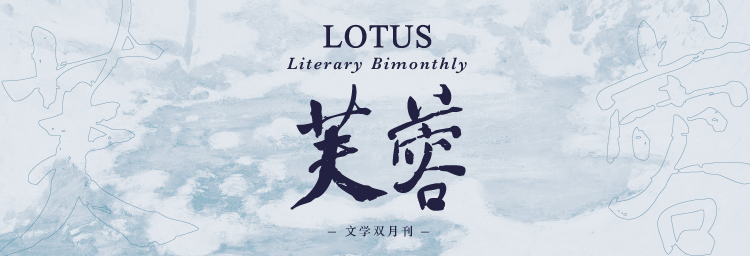

上垭下垭(中篇小说)
文/向本贵
一
刚下车,邹心妹就看见了他,上垭村那个当了一辈子村主任的李生柱,默默地站在一群乡村干部的后面。邹心妹的心里不由一阵战栗,她差点就认不出他了,曾经牛高马大的壮实汉子,被岁月的风霜雨雪摧残得不成形了:满脸沟壑般的皱纹,一头杂乱的白发,背还驼得厉害。可他却没有认出她来。目光在几个扶贫工作队员之间流连,沧桑的脸上,除了满布着慈祥,就是满满当当的企盼和期待了。
半塘乡党委周书记一一跟大家握过手,吩咐乡干部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过后把手一挥,说:“都去会议室,开一个简单的会。”
村干部们连忙让开一条道,等着市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员先进了会议室,然后才跟着进去,默默地坐在一旁,眼睛还是盯着他们不松开。
市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员共有七个人,女的却只有邹心妹一个。前些日子单位开会,领导说市里要派扶贫工作队去昭阳县半塘乡扶贫,时间一年,几个大局各派一个人,她没半点犹豫就报名了。坐在欢送扶贫工作队来半塘乡的面包车上,她还有点发蒙,她只记得,当时单位领导说半塘乡三个字的时候,她的脑壳里面闪过一个人影,一种莫名的冲动倏地在心里复活,不揭开潜藏于心底的疑窦,实在心有不甘。
“扶贫工作队七个人,包括我这个扶贫工作队长,都不住在乡政府,全部下村里去。”扶贫工作队长将六个扶贫队员一一做了介绍之后,看着乡党委周书记,这样说。
“七个贫困村的领导全在这里候着呢。”周书记将七个贫困村的情况介绍了一番,要扶贫工作队员自己挑,“要说七个贫困村,离乡政府最远的是上垭村,工作难度最大的也是上垭村。”
“我去上垭村吧。”
周书记的话没说完,邹心妹便抢着这样说。周书记看了她一眼,过后就把眼睛盯着坐在角落里的李生柱。
“邹干部啊,你还是别去上垭村了。过去人们见着上垭村人,都要捂着鼻子,说上垭村的人身上有一股臭气,如今水的问题解决了,身上的臭气当然是没了,可路还是没通,高跟鞋爬不上去象鼻子崖的。”李生柱还真不乐意让一个女干部去上垭村。乡党委周书记早就对他交了底,市里的扶贫工作队下来,给上垭村分一个,抓住难得的机会,把路修通。去一个脚穿高跟鞋、涂脂抹粉的女干部,没能力弄钱修路,只怕还得照顾她。
他果然没认出自己。邹心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板着脸说:“瞧不起我是吧。”
李生柱有点尴尬,连连摆手道:“不是那个意思,女同志去上垭,的确不怎么方便。”
周书记在一旁说:“去上垭村不用操心扶贫的事,全村二百多户,没有建档立卡需要脱贫攻坚的特困户,即便一些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扶贫工作队员去了就一项工作,弄钱修路。”周书记的眼睛盯着邹心妹,意思再明白不过:村村通公路,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上垭村的公路却没有修好,可见难度之大,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没有料到,几个扶贫工作队员却是异口同声道:“还别说,工作难度最大的村,还真得邹科去才行。”过后,他们就挤眉弄眼地说,“邹科去了,修路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不然,我们中间无论谁去,还得说好话求她帮忙。”
邹心妹瞪了他们一眼,把一个大帆布袋子背在背上,脚步噔噔地出门去了。
周书记追着她的背影说:“要去上垭村也行,还是住在乡政府吧,隔三岔五去一趟上垭就是了。”
邹心妹没有搭理他的话,只是狠狠地瞪了跟在后面的李生柱一眼。周书记只得叫来乡政府的小车:“快去,送送他们。”
小车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颠簸了老大一阵,再没有往前走,而是转了个弯儿,爬上一道陡坡,那条逼窄而陡峭的岔道戛然而止,小车也只得停了下来。
“离上垭村不远了,只是那座象鼻子崖特难爬上去,要不我送送你吧?”小车司机是个打扮时尚的年轻人,这样说的时候,用指尖顶了顶架在鼻梁上的宽边墨镜,还不忘把自己刚刚剪过的飞机头往上捋了捋。
“快回去吧,他们都还等着你呢。”邹心妹这样说过,背着背包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崎岖小路往山上爬去。
正月,没有一丝暖气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带着寒意的山风从林子里拂过,几片枯叶掉在了邹心妹的头上,她也没有摘一摘。她已经气喘吁吁,还有星星点点的汗水从额头鼓出来。跟在后面的李生柱伸过手,也不管她同意不同意,抢过背上的背包背在了自己的肩头。
“我的意思,你该去前坡村或是半湾村,离乡政府近,工作难度也没有上垭村大。”
李生柱还说了些什么,邹心妹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的目光被山坡旁边的村落牵引过去,心跳不由得也在加速。正月初七,单位上班的日子。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春节的七天长假,对于上班族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打算,新的希望,新的憧憬和成就。
农村却不一样,正月不完还是年。远远看去,各家大门上的大红对联在斜阳里熠熠生辉,几缕炊烟在屋脊上缠缠绕绕,空气里似乎还能嗅到肉香酒香。突然,半空中散开一团淡蓝色的烟雾,像是一朵绽开的黑色牡丹,后来,才听到啪的一声炸响和孩子们的嬉闹之声。小孩过年时玩的钻天炮还没放完呢。
邹心妹的目光从高高矮矮的屋宇和几栋新修的砖房中间移过去,就看见了那栋破旧的木屋,那曾经是她的家,她在那栋木屋里度过了苦乐掺杂的童年,上学了,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家。十年前母亲去世,父亲把木屋卖给了邻居,随她进城去,就算是跟这个叫作下垭村的地方彻底告别。人说乡愁难解,她心里的乡愁却是复杂得难以言说。
“下垭村早就通公路了,上垭村的人们要想见着汽车开进村里去,如果国家不伸手帮扶一把,少说也要再等十年才行。”李生柱的眼睛依着邹心妹的目光对着下垭村看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说。
邹心妹没有理会他说的话。汗水在她的脸上聚成了几条沟儿,簌簌地流淌下来,脚上的高跟鞋在陡峭的山路上歪歪扭扭着。李生柱再没说话,只是勾头对着她的脚上看了一眼。邹心妹伸手要过李生柱背上的帆布袋子,从里面取出一双黄跑鞋穿上,嘴里说:“村村通公路,是新农村建设的硬指标,上垭村的路怎么还没修通?”口气冷冰冰的。
“县里来的扶贫工作队,把交通部门的技术员请来看了看,听说要几百万资金才能劈开象鼻子崖,一个两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哪有能耐弄到那么多钱。”李生柱抬起头来,深眍下去的眼里闪过一缕光亮,“去年腊月在乡政府开会,周书记说这次是市里来的扶贫工作队,或许能弄到几百万块钱给上垭村修路,要我不能像前几次那样,拒绝扶贫工作队去上垭村。邹干部,真要帮着上垭村圆了修路的梦,上垭村的群众会感激不尽。”
“你刚才说,国家要是不伸手帮扶,上垭村的人们想看到汽车开进村去,还要等十年,什么意思,十年之后路就通了?”
“就这样等着,盼着,心里着急呀。去年冬天,我们把村里没有外出打工的中老年劳动力组织起来,自己开始动工修路了。只是进度太慢,没有十年是劈不开象鼻子崖的。”
李生柱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邹心妹的眼泪却是抑制不住簌簌地淌落下来。她看见了前面山腰上的那座坟茔。这一路来,她一直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掉眼泪,不值。可是,看见那堆黄土,她还是哭了。她娘就躺在那堆黄土下面。
十年前的中秋节,一个特好的天气,城里难得见到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邹心妹把月饼和水果摆在阳台上,招呼男人和才两岁的儿子出来赏月,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却唱起歌来,是父亲打来的。邹心妹说:“爹,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大前天寄回去的月饼收到没?中秋节单位搞活动,没时间回来了。”邹心妹从懂事的时候起,对娘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隔膜,跟父亲却是格外亲近,平时打电话,也就顺带着问娘一声,今天,却是连问一声都没有。
“心妹,你快回来,你娘被五步蛇咬了,快不行了啊。”父亲说得急促,还带着哭腔。
“怎么被五步蛇咬了,中秋节,她又去了哪里?”邹心妹知道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农村,被五步蛇咬伤必死无疑,可她没有半点惊恐和心疼,说话的口气冷冰冰的。
父亲没有回她的话,把电话挂上了。邹心妹坐着发了一阵呆,对丈夫赵明启说:“我得回去一趟,她被毒蛇咬了。”
“谁被毒蛇咬了?”赵明启把儿子抱在怀里,正教他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除了儿子的外婆,还能有谁。”
赵明启就着急了:“赶快送医院去抢救啊。”
“五步蛇咬的,还没到医院,只怕早就没气了。”
“那你还愣着做什么,现在就走,带着儿子,我们一块儿回去。”
“不,你在家带好儿子,我明天就回来。”说完这话,邹心妹又对男人怀里的儿子说,“把床前明月光背熟,我回来给你买变形金刚。”
赶到家,已是半夜转钟,娘已经死了,样子十分痛苦:瞪着眼,张着嘴,那只被毒蛇咬伤的脚肿得像冬瓜。爹哭得死去活来,还不停地对女儿诉说着娘这辈子对他的种种恩爱。邹心妹没有哭,也不愿意听爹爹说的那些话,她甚至觉得爹爹这辈子除了窝囊,就是可怜。
把娘送上山,清理娘的遗物时,邹心妹在娘的背篓里发现了两个月饼。大前天邹心妹寄回来一盒月饼,是那种市面上卖得比较贵的月饼,只有四个,却要二百块钱。家里只留下两个,居然给那个人两个。爹爹不说,她也能猜得出来,一定是去上垭的路上,不小心被五步蛇咬了。死了活该。
邹心妹说的那个人,就是眼前的李生柱。上中学之后,邹心妹就再没有见到过他,算一算,快三十年了,但在她的心里,他就是化成灰,她也能认出来。刚才见着他时,她还想呢,岁月的风霜雨雪,居然把一个面目端正,身材魁伟的男子汉,磨砺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邹心妹心里不由一阵战栗,偷偷地瞅了老人一眼。多少年了,她一直怀疑跟着自己住在城里的那个父亲,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面前的这个男人跟自己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次来半塘,她就想着能不能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没有想到,这一年里她就住在上垭,要天天跟这个与自己的身世之谜纠缠不清的老人打交道。
“邹干部,你先在上垭住些日子,要是不习惯,还是住乡政府去,隔些日子来上垭打个转就是了。”
“还没问你,上垭村是个什么情况?”
“我不是说过的吗,要想再往前走一步,除非把公路修上山去。”
邹心妹冷冷地说:“我是问你上垭村的基本情况。”
“全村二百二十八户,九百八十一口人。年轻人大都去城里打工了,过年才回来打个转。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因病致贫的人家,当然也是有的,不过都已经得到了扶持和照顾,吃饭穿衣不愁。只是,村里的五保户多了些。那时上垭穷,讨不到女人,打单身的多,现在就都成了孤寡老人,衣食住行都要村里照顾着。”
“如今上垭村的年轻人能讨到女人了?”
“当然。”
“村里真的没有建档立卡需要扶持的特困户?”
“没有。”李生柱沧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笑意,回答得也格外响亮。
邹心妹对他的这种笑十分反感。这么得意,还要我来上垭帮着弄钱修路做什么?过了一阵,她又问道:“路不通,村里就没人想着要往外面搬?别个偏远落后的村寨还整个往外面搬迁呢。”
“曾经有几户人家在镇子上买了房子,举家搬到镇子上去了,只是,没住上几年又都搬了回来,说还是住在上垭好。”说这话的时候,李生柱就变得脸红脖子粗了,“乡里的领导是动员过上垭村举村往外面搬迁的,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我,三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在上垭落脚生根,修房屋,造梯田,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说走就走了?”
爬上一条长长的坡坎,一道刀砍斧劈般陡峭的崖壁就墙一般挡在面前。邹心妹知道它叫象鼻子崖,可她至今也不知道这道崖壁为什么叫作象鼻子崖,叫作门板崖或是墙壁崖倒是再贴切不过。邹心妹不可忘怀的,不是这道崖壁有多高,有多陡,横亘在大山中间,把一座莽莽苍苍的大山生生地分成了上下两半,也不是崖壁上开凿出来的那条逼窄险峻、千足蜈蚣一样的小道,而是崖壁下面的那棵老酸枣树,那棵老酸枣树枝繁叶茂,硕大无朋。每年的八月,满树的酸枣从青涩变成了金黄,微风吹来,空气里氤氲着浓浓的酸甜味儿。将掉在地上的酸枣拾来塞进嘴里,可口极了。当然,邹心妹也没有对酸甜可口的酸枣留存多少记忆,她是在酸枣树下,发现了娘的那个秘密。
第一次看见娘跟李生柱在一起,是邹心妹四岁的时候,是中秋节。那时外婆还健在,娘说要去外婆家,却不带父亲去,也不让她去,一个人背个背篓匆匆走了。邹心妹在后面追赶,还哭。父亲好不容易把她哄回家,还煮了个鸡蛋给她吃。趁着父亲做活的当儿,她还是偷偷地追赶娘去了。
娘和李生柱相对着站在酸枣树下,娘的两眼看着李生柱,像是看不够似的,后来,就有两行泪水挂在了脸上。李生柱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抬起手想揩去娘脸上的泪水,手还没挨着娘的脸,却又缩了回来。邹心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跑过去,抱着娘哇哇地哭起来。娘的那张凄凄楚楚的脸立马就变得十分愠怒了,娘扬起手,狠狠地给了她一耳光,嘴里还不停地骂:“叫你别来,你跟来做什么。”
李生柱却是一边哄她,一边给她拾酸枣吃,过后,还从口袋掏出五块钱给她,要她去乡场买糖果,爬象鼻子崖的石级时,也不让她走,他背着她,一直把母子俩送到外婆家的禾场前才离去。下午从外婆家回来,娘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骂她了,还变着法子哄她开心:“回去之后,别对你爹说看见他了,也别说他给了你钱,那钱你自己留着买糖果吃,娘也不要你的。”
那时,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都还没有从穷困中缓过气来,五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邹心妹看了娘一眼,娘正用讨好的眼神看着她。她说:“不说就是了。”
后来,娘说要去外婆家,她总要悄悄地跟了去,当然是一定会看见娘跟李生柱在一块儿的,当然还是在象鼻子崖旁边的那棵酸枣树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即便有人路过,往硕大无朋的酸枣树背后斜一斜,就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每次,娘站在李生柱的面前,总像是怎么都看不够似的,后来就哭,眼泪像是山泉水一样流淌。当然,邹心妹再不敢过去问娘为什么要哭。讨打啊。她心里那种恨却是愈加强烈,恨娘,还恨李生柱。当然,还十分同情爹爹。娘外面有个野男人,莫非爹爹就不知道?
长大之后,邹心妹才隐隐约约知道,李生柱是娘曾经的相好,两人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还山盟海誓呢,可娘却嫁给了父亲。邹心妹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着,悬在半空中就没有落下过。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是谁的女儿。当然,对父亲的同情就又多了几分,对母亲的恨更是无以复加。
让她自己也觉得可笑的是,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心里的那种恨似乎淡了许多,一种想要破解身世谜团的愿望却愈加强烈起来,怎么说,总不能活在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的阴影里吧。
“邹干部你不知道,上垭下垭,也就隔着一道象鼻子崖,那时人们的日子却是有天壤之别。上垭人总是为没饭吃发愁,到了春荒时节,山里能吃的树叶和草根都采摘光了,就只得四处借粮。下垭却不一样,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不愁温饱的问题。上垭人见了下垭人,老远就露出讨好的笑来,指望下垭人能伸出援手,借一斗半斗粮食帮着度过春荒。即便如今,上垭的日子过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可人家下垭还是走在前面,木屋变成了砖房,公路修进了村,小康路上正跑得欢呢。上垭人进进出出,还得用两脚丈量这崎岖的小路,弯着腰爬这陡峭的崖壁。”李生柱的话转了一个大弯,为的就是要引出修路的话题来,“要说我们一心靠着国家帮我们劈山修路也不对,这么多年来,我们先是忙着劈山修渠,把老狼谷的山泉水引进村来,解决田地十年九旱和群众吃水的问题,接着,又着手整顿村容村貌,改造危房,维修村道,直到去年,才腾出手来劈山修路。到了上垭通车的那一天,还不知道下垭村的人们已经过上多好的日子了呢。”
邹心妹果然看见了,酸枣树旁边的崖壁上,已经劈出了一段车道来,斜斜地向着那边的崖壁延伸过去。
“悬崖峭壁,猴子都挂不稳,靠着自己腰上缚根绳子,手握钢钎铁锤凿开一条四米宽、八百米长的车道,谈何容易。”李生柱眼巴巴地看着邹心妹,“要是市里能弄到钱来,请个专业的修路工程队,一年两年,汽车就开到上垭村了啊。”
邹心妹却是冷冷道:“今天天气很好啊,城里的上班族都上班了,你们还在过年呀。是不是知道市里的扶贫工作队要来,就靠上了。”
“没。大年初一就来劈山修路了。昨天老伍头的一只脚被石头砸伤了,我就让大家今天休息一天。这些日子,都很累了。”
邹心妹再没有理睬他,她早就爬得上气不接下气,要不是肩头的帆布袋子再一次被他抢了过去,只怕早就两脚发软,瘫坐在悬崖峭壁的石级上起不来了。
二
上垭村的样貌,邹心妹只能依稀地记在脑海里。攀着绝壁上的石级小道,爬上象鼻子崖,眼前豁然开朗,层层梯田向山腰伸展,梯田的上面,是一片一片旱地。一条茅封草长的小路,向着梯田旁边的村子延伸过去。远远看去,破烂的木屋像是被太阳晒蔫了的野蘑菇,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在田地里辛勤地劳作,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田地里的禾苗也如这些劳作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在风雨里摇晃着瘦萎的身段。
邹心妹的外婆就住在那边山腰的一棵板栗树下。曾经听娘说过,外公去世早,外婆含辛茹苦把她养大成人,泪水洗面,衣角包米。邹心妹对外婆的记忆却是十分模糊,她只记得外婆个子矮小,还很瘦,一件破旧的衣衫穿在身上好像从来就没有洗过。整天还用手按着胸口,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让邹心妹不可忘记的,是她六岁的时候,外婆去世,是李生柱去下垭送的信。邹心妹看到李生柱,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憎恶,她真想对爹爹说出娘跟这个男人的秘密,可是,她还是不敢,担心娘往死里打她。只是把眼睛瞪得老大,她觉得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娘哭哭啼啼跟着李生柱在前面走,父亲牵着她的手走在后面。她催父亲快点走,跟上那两个男女,父亲却是有意无意地越走越慢。
来到外婆家的时候,娘抱着外婆哭得死去活来,李生柱像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一样,帮着忙这忙那,不时地还跟父亲商量一些当紧的事情,父亲总是依从地点着头,脸上还流露出感激的神色。邹心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说:“爹爹,我要对你说个话。”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呢,爹爹却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忙他的去了。邹心妹一直没有弄明白,爹爹为什么要那样瞪自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不让说呢,还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听。在她看来,爹爹除了格外喜欢自己,对娘似乎也更加疼爱了。
邹心妹已经找不着记忆里的上垭村了,除了层层梯田和片片旱地还是那样平平静静地摆在蓝天之下,那条弯弯扭扭的田间小路,已经变成了平整而宽敞的水泥道,一直往村子延伸过去。村子也大变样了,果树成荫,村陌干净平整,过去破烂的木屋也都修缮一新,屋顶上的茅草换成了青瓦,壁板用桐油油过,在正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过年贴的大红对联格外惹人眼目。村子的中间,还有几栋新修的砖房,红墙青瓦,甚是气派。邹心妹还在想呢,这样漂亮的村落,跟大山外面那些早已步入小康生活的富裕村寨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突然,一阵童稚的叫喊声随风传来,一群衣着艳丽的孩子手里拿着一片红绸布,从村里跑出来,并排站在村口的水泥路上,大声地叫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手里的红绸布在正月的阳光下像彩蝶一样飞舞。
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站在孩子们的身后,灿烂的笑脸绽开如一朵芙蓉花儿,她大老远就伸手把李生柱肩头的帆布袋子接了过去,嘴里说:“欢迎市扶贫工作队来上垭村扶贫啊。”
邹心妹心想,这些孩子一定是她组织的吧,她是上垭村的什么人?
李生柱可能看出了邹心妹的心思,说:“她叫王秀芬,上垭村的妇女主任,全村就数她家的条件最好,这一年你就住在她家里。”过后对王秀芬说:“邹干部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累了,弄点饭吃,让她休息一会儿,晚上开会,上垭村的群众等着要见见市里来的扶贫工作队的干部呢。”
“还是住在李伯家吧,商量工作方便。”邹心妹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把李生柱叫作李伯?也许,当她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心里除了恨,还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愫。他已经老了,当年高大威猛的壮汉已经不再,当她爬上象鼻子崖,走进村里的时候,这种情愫又增加了几分,上垭村大变样了,还真是苦了他啊。
李生柱连连摆手说:“家里那个样,你住不习惯的,再说,我一个人,吃饭从不讲究,一个菜一碗汤是一餐,一个红薯一个苞谷也是一餐。秀芬家离我家不远,有什么事情,叫我一声就是。知道吗,秀芬是我们上垭村年轻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还贤惠善良,识大体,明事理,是我培养的接班人。我老了,过一年两年,我就把村里这副担子交给她了。”
邹心妹没有理睬他,对王秀芬道:“走啊,还站着做什么?”
王秀芬只得把跳着唱着的孩子们交给跟着来看热闹的一群老人,带着她往村子旁边一栋破旧的木屋走去,嘴里说:“生柱伯一辈子忙着村里的工作,自己的房子也顾不上整修一下。”
“一个人住,下雨天不漏雨就成,要整修什么。”李生柱过后有些为难地说,“邹干部,住在我家还真的不行呀。”
邹心妹手一挥,对着王秀芬道:“帮帮忙,把厢房打扫一下,开个铺,我就住在厢房里。”
王秀芬开始还愣在那里,过后就动手帮着打扫厢房,理床铺被子:“先在这里住几天,要是觉得不方便,还是住我家里去。我家里人也不多,我和我儿子,还有我儿子的爷爷奶奶。”
“你男人打工去了?”
“不去打工,日后儿子读书哪来的钱。”
“听口音,你不是上垭人?”
“不是上垭人,也不是半塘人。”王秀芬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打工遇着我儿子他爸,怎么会到这里来?”
“后悔了?”
“进山出山,就得过象鼻子崖那道坎,我数过,二百二十八道石级,像天梯。不过,现在习惯了,在这里过日子还是挺不错的。村子干净整洁,山泉水引到了灶头,水泥路连接着各家各户。不愁吃,不愁穿。”
“你还没说是哪里人啊!”
“武陵山腹地。说起来,我的家乡比上垭更加偏远落后,可公路却是修进村了。”王秀芬脸上的愁容转瞬间又变成了好看的笑颜,“这些日子,人们说的就一个话题,市里的扶贫工作队来我们村,要是能弄来资金把公路修上山,就不用我们自己抡锤劈石,再花十年时间才有一脚好路走。听我儿子他爷爷说,为了把老狼谷的山泉水引进村来,生柱伯带着全村的劳动力,用了整整十年,硬是从一座石头山的悬崖峭壁上劈出一条水渠。人们都说了,扶贫工作队能把上垭的公路修通,我们就给他立功德碑。真的没有想到,是你邹干部啊。”
“失望了?”
“才不。扶贫不分男女,也不在年纪大小,只要实心实意,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收拾停当,李生柱已经把晚饭做好。王秀芬没有走,对着桌上的饭菜看了一眼,笑靥如花:“生柱伯,你做的菜怎么全是我喜欢吃的。”
李生柱却是问她道:“还没问你,你爹的脚好些了没?”
邹心妹说:“生柱伯说昨天修路时一个老人被石头砸伤,原来是你公公啊,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敷点草药,包扎好,不多日子就好了。不用邹干部挂记的啊。我儿子他爷爷说,那阵修水渠,生柱伯的脑袋被石头砸了一个洞,鲜血直流,他也不肯休息,从衣衫上撕下一块布条包扎一下,就又抡锤打炮眼了。邹干部你不知道,生柱伯说今天要去乡里接市里的扶贫工作队,我儿子他爷爷就像是吃了笑鸡婆肉,乐开花了。”
李生柱却是不再说话,把一条鸡腿和一个鸡翅夹到邹心妹碗里,又给王秀芬的碗里夹了些鱼和肉,说:“快吃饭,吃过饭还去对大家说一声,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不要迟到,更不能缺席。修路的事我早就对邹干部说了,还说,人家耳朵都要长茧子了。”
王秀芬道:“还要再去说啊,人们早就等不及了,说不定这时就有人在会议室候着呢。”
邹心妹有几分感动,还有几分意外。不论小的时候,还是现在,她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腿和鸡翅。也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家里杀鸡,谁都不能吃鸡腿和鸡翅的,父亲早早就把鸡腿和鸡翅夹在她的碗里了。这个李生柱,居然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喜好。
她把鸡翅夹给了王秀芬,说:“我们俩各吃一样。生柱伯,你自己也吃。”
王秀芬看了李生柱一眼,又把鸡翅退给了邹心妹,说:“生柱伯原本就没有给我做打算,一只鸡,两条鸡腿,两个鸡翅,为什么碗里只有一条鸡腿一个鸡翅?给你留着的啊。”
李生柱又把几块鸡肉往王秀芬的碗里夹,脸上满布了慈祥,嗔她说:“邹干部第一天在我家吃饭,要跟她争呀。”
王秀芬又把一块鸡肉夹到邹心妹的碗里,嘴里喃喃:“实在说,上垭村除了进进出出的路难走,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真不错。生柱伯挂在嘴边的话,就担心路没修好,他却是动不得了,要交班了。现在看来,这路还是会在生柱伯的手里修好的。”
李生柱坐在一旁,饭也不吃,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邹心妹,像是看不够似的。王秀芬就又把嘴噘了起来,几分娇气地道:“路不修通,我不会接这个班的。”
邹心妹一边吃饭,一边想,这一老一小,倒像是一对父女啊。
一餐饭吃到天黑,李生柱对邹心妹说:“去开会吧,这时,大家真的都等着你呢。”
王秀芬突然像是想起什么来,对李生柱说:“上午通知大家晚上开会的时候,去郑爷爷家看了看,郑爷爷说他的大米又吃完了,还哭呢,说他怎么就不死,老是要麻烦你去乡场给他买米。”
李生柱叹了一口气:“国家的政策好,每个月给五保老人三百多块钱。问题在于,这些五保老人拿着三百多块钱当不得饭吃,还得变成油盐柴米,我一个月要往乡场跑几趟,有时爬象鼻子崖实在累得不行,只有让秀芬也帮着去乡场背。”
邹心妹心里说:“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看来,不把上垭村的路修通,我这个扶贫干部是走不脱身的。”
会议室里人头攒动,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挤了一屋子,炭火烧得正旺,空气里还氤氲着瓜子、花生和糍粑的芳香。让邹心妹没有想到,偏远山村,村委会议室却是这样的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壁板上的宣传栏也布置得别出心裁、光鲜漂亮,像是山村姑娘的挑花绣朵,养眼。在宣传栏前流连片刻,邹心妹对上垭村的基本情况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王秀芬说:“宣传栏是我弄的,水平不高,村里的许多事情也不能一一写上去,明天我带你去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各家各户的木屋都用桐油油过,锃光发亮,就连猪栏厕所,生柱伯都有要求,不能当街当面,化粪池,垃圾坑,更是严格标准。整个村子,但闻鸟语花香,谷物瓜果芬芳。生柱伯就一句话,住木屋也要住出样子来。”
邹心妹却道:“我更关心的,除了你们说的那条路,是村里的贫困人家,是需要帮助和扶持的困难户。上垭村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全都脱贫致富奔上小康生活了?”
王秀芬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被李生柱拦住了,他说:“建档立卡的特困户的确没有,因为天灾人祸,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家还是有的,这些人家离小康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明天让秀芬带着你先走访这些人家,给他们出出主意,如果能弄到一些扶贫资金来,让他们做一些发家致富的项目,小康路上的步子也就走得更快了。”
不知道是大人的暗示,还是孩子们的自觉行为,一个小女孩把一颗糖果剥好塞进邹心妹的手里,过后,一群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给邹心妹递瓜子、花生。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烤得香喷喷的糍粑,想递给她,却挤不进来,只得远远地站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她,脸上透出腼腆的笑。邹心妹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儿子今年十二岁,也有他这么高,这么结实,这么可爱,现在,儿子或许正跟着外公和爸爸一块儿坐在电视机旁看电视吧。伸过手,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问道:“叫什么名?”
“李从军。”
“多大了?”
“十二岁。”
“明年就是中学生了啊。”
李从军却不再说话,两滴晶亮的泪水从眼里鼓出来。邹心妹不由大惊:“你哭什么?”
“我想请邹阿姨把路修好,我读书就不担心再在象鼻子崖摔跤了。”
王秀芬挽起李从军的裤脚说:“读一年级的时候,腊月天下大雪,星期六回家爬象鼻子崖,脚下一滑,掉下崖壁摔断了腿,虽是接上了,却留下了残疾,这辈子参军的梦想是没办法实现了。你不知道,他爹就希望他日后长大了去当解放军。”
“扶贫工作队来过几次了,都说弄不到那么多钱,你只怕也是嘴里说说吧,一年过去,拍屁股走人,白让我们高兴一阵子,到头来,还得李村主任带着大家腰上缚根绳子,挂在悬崖峭壁上自个儿慢慢劈崖修路。”说话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站着的时候,身子向一边歪着。
王秀芬过去扶着老人坐下,说:“爹你别着急,这次跟前几次来的扶贫干部不一样,答应了,是会算数的。”
邹心妹这才知道他就是昨天修路时被石头砸伤了脚的老伍头,王秀芬的公公,笑着说:“伍伯,我原本是要去看望你老人家的,吃过饭,天就黑了。在这里,我要向你老人家问候一声,辛苦你老人家了啊,好好养伤吧,往后,决不会让你们腰上缚根绳子,挂在悬崖峭壁上劈石头了。”过后,她紧紧地把李从军搂在怀里,一字一顿地说,“不把上垭村的路修好,我就不走。”(节选自《芙蓉》2021年第4期向本贵中篇小说《上垭下垭》)

向本贵,苗族,1947年生,湖南沅陵人。一级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苍山如海》《凤凰台》《遍地黄金》《盘龙埠》《两河口》等十部,小说集《这方水土》《向本贵小说选》《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向本贵卷》等四部,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曾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有四部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