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蔡测海:西藏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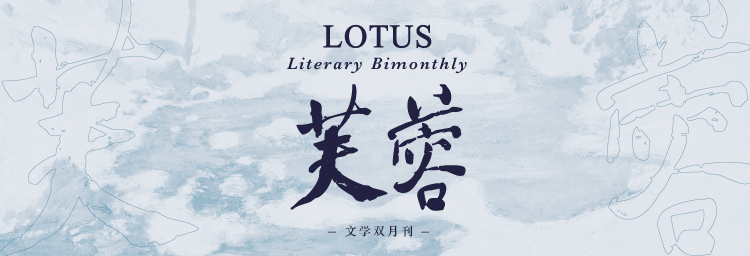

西藏西(短篇小说)
文/蔡测海
我的这个念头,来自我和一条狗的对视。
它当然是中华田园犬,这样的狗才是一条真正的狗。它有豹子一样的身段,豹子一样的耳朵,通灵的鼻子。狗的灵魂在眼睛的深处。我在小说《留贼》中写过它。黄狗,凡·高的向日葵的那种颜色。这颜色,代表奔跑的激情,像在时间里奔跑的一束阳光。日落时分,我和它站在夜岚来潮的山冈上,我俩相互凝视。一条狗要真的看你,你不会低,也不会高,我看到了自己,我是个善良的人。我想,它是不是也这样打量一头野兽?那么,我是人是兽就不太确定。
我已经不记得它的名字,我也从不叫它的名字,也许它根本就没有名字。一条真正的狗为什么要有名字呢?比方叫它招财、来福,对得起狗吗?哪怕你叫它白比姆黑耳朵呢。
我和它去过很多地方。我喜欢去的地方,它都喜欢。我去二姨娘家,它跟着去。经过一些森林,庄稼地,几处村落,再沿酉水往上游走,到一个叫上鱼潭的地方,这儿是二姨娘家。外祖父外祖母的坟也在这里。我母亲的出生地也在这里。也可以说,这里也是我的出生地。母亲在这里出生,然后,她带我到别的地方出生。出生地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因为我并没有关于出生的记忆。
我去祭拜外祖父外祖母的坟,黄狗就在一旁伏卧,像做个仪式。
二姨娘半瞎,二姨父去世早,她讨过米,所以很怕狗。我的狗其实对二姨娘很亲热。二姨娘家在河边,能吃到酉水鱼。鱼骨头是猫狗最喜欢的。那时候,酉水河里鱼真多。做饭时架锅,大表哥就从河里捕一条大青鱼来,像从菜园子里扯个萝卜一样。
后来,酉水河鱼很少。以往的事就像撒谎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我和黄狗到过二姨娘家,我们离开,一切不见痕迹。只是说起来到过那里。那些踪迹,于这世界,已可有可无。后来,二姨娘也去世了。酉水也再不是二姨娘在世的那条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怕狗或者不怕狗,天晴落雨,河鱼的美味,都成过去。出生地是记忆性的,也终归终止和消失。
我之所以要写一条狗,并非因为它与我的命运有多么重要的联系。我们是两个生命。没有那次在山冈上的对视,我们也会活在各自的时间里,我写它,是因为它有一种超乎人类的记路本能。有“猫记百里,狗记千里”的说法。一条狗走多远,也能记住往回走的路。它没有人的那种标路记路的办法。狗是怎样记路的?它在岔路口会用鼻子闻一下,它的记忆力可能在鼻子上。我确定信任它的鼻子。它用鼻子辨识长路,也辨识别的事物。满世界对鼻子来说,只有香的和臭的。不怕香,不嫌臭,别的气味,也一闻知远近。我为此写过狗鼻子歌。
狗鼻子陪我上学放学,陪我拾柴,找山货。我久病的日子,它陪着我,跟我找名医张安子。因为是去求医,它不与主家的狗斗狠,不张牙,不竖尾。只是威武地站着,摆出狗的尊严。张安子给一位少妇把过脉,然后来问我的病情,没把脉和看舌苔,给讲了一些医德方面的话,给我开药,一截芦根,临从他的草药园采来。
我谢过名医张安子。他指着我的狗说,这狗真肥壮,黄狗肉比麻狗肉好吃。我对黄狗说:快走,我们回去。
回去到半路,天黑下来。灵官庙爬坡,冷冷的夜风。狗在前边探路。这里大军剿过土匪,水沟里躺了许多尸体,水是血水。天阴转晴时,还能听到机关枪的响声从石壁里传出来。月光下,我和狗和我俩的影子成伙成众,不怕鬼。
走夜路,怕长鬼。长鬼见人,长高长大,倒下压人。有狗,长鬼会变矮,变成牛屎堆。一路上是见过牛屎堆的。它们是被狗降伏的长鬼。鬼有各种颜色,病死鬼是黑色的,吊死鬼是白色的,凶死鬼是红色的。有狗做伴的那些年,我没见过鬼。
上学。老师是地主子弟。山村小学的老师,有很多是地主富农子女。穷地方,有钱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解放了,他们教穷人的子女读书。土改斗地主分浮财,那些先前的有钱人家,留下的财产就是读过的书。留着,再慢慢分给我们。
老师不喜欢狗,见到狗就皱眉头。二姨娘是穷人,讨过米,被狗咬过,怕狗。老师先前是大户人家,养狗看家护院,他怎么会讨厌狗?那次,乡邮员捎口信,他家出事了,太太要他回去处理。家里一钵子猪油让狗吃了。那年头,一钵猪油有多珍贵?吃油要油票,每个月才四两菜籽油。太太要他回家,是不是要把狗杀了?
狗跟着我上学,我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后来老师家出了事,我不想它跟我上学,对它也讲不明白。走到叫桂花坪的那里,我把带到学校吃的中饭放在一块石板上,对狗说:在这里等我放学回来。
等我上完第一节课,它叼着饭篓子,在教室门口,见我出来,直摇尾巴。我到哪儿它跟哪儿,它不跟我进教室。它知道,那是它不能去的地方。
我读完小学四年级,它在教室门口趴了四年。它没听懂我学的功课,还是记住了每节课的时间,四十五分钟。不等下课铃响,它就会站起来摇尾巴。它还记住了学校的模样,灰瓦的木楼,秋千,几棵大枫树,一片紫竹林,还有半边篮球场,以及球场上的游戏,跳绳,跳房子,撬飞棒,踢毽子,捡子和牵羊羊,丢手绢。它会参加丢手绢的游戏,叼着手绢放在别人的身后。
后来,它突然消失了。以前,它也消失过几次,几次都是受伤回来的,一定与什么野物经过生死搏斗。黄毛染血,凡·高的向日葵变成了莫奈的落日。每次负伤,我都用金创药给它治伤,就是把青蒿叶或鱼刺蒿捣烂敷上。我会制金创药,是因为刀斧伤人是常见的事。
最后一次,它真的消失了。我想它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来。没约定什么地方,它会在某个地方和我见面。
生活就像一条狗,有事无事汪汪叫。于是,人就学狗叫,这话,我是在去某处,在凉亭子里歇口气,听路人说的。这是胡说,我那条狗从来不叫,它不想被骂。想它以后也不叫,像时间一样沉默。
我有位朋友写诗,给我说两句:
乡下的狗子成群
见不相识的便狂吠
我很生气,怎么能这样写狗诗了?不是说要生活吗?一个没有见过狗生活的人,就不要乱写诗。朋友也生气了,对我骂脏话:好吧?你去当兽医吧!
我知道,很多人写诗,是因为心理疾病,容易激动。除了高歌就是骂。我理解,心里不顺,写几句诗,可以原谅。不必拿他比王维或李商隐。朋友和我一样,没读什么书,能写几句诗已经很好了。这不怪我们,大家都很忙。
很忙。记性也越来越差。说记性让狗吃了,真的想狗把记性吃了。狗的记性好。
后来。后来已是从前。
从那位地主子弟那儿,分到的纸上浮财,散失殆尽。神话里的东西——阿拉丁神灯,龙王爷的聚宝盆,王母娘娘的枕头和仙女,马良的神笔,太上老君的丹药,张天师的拐杖,四大菩萨,封神榜上那些神仙……一个也没帮我。为了吃饭,我学了几年手艺。先学木匠,泥瓦匠,裁缝,钟表匠,再学耍猴,唱傩戏,草药匠,最后学会弹棉花,做弹花匠。本来还想学养蜂,偷蜜,却被师傅清理门户,罚我吃一个月蜜,真的是甜也难吃。后来一听到糖,马上昏迷,连翻白眼都来不及。
弹花匠,四处乱窜。吃百家饭。不等你看破红尘,红尘早把你看破了。你不做黑心棉,人家也防你像防流行病。
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少了一条狗陪着。以后也不会再有一条好狗的命了。中华田园犬,凡·高向日葵。往事就像谎言。曾经的生活,就像没人看管的牛,被盗牛贼顺手牵走了。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都有名字,我就是找那些地名去的。离开的时候,再无某地的名字,不再记它。所有的地方,叫什么名字都一样,就是弹棉花,吃饭。弹花匠不是徐霞客,不必记地名。如果我是说书的,人名关口才有用。
到一处叫白帝城,千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满巷夕阳的地方,居然遇见儿时伙伴索马里。彼此相见一愣,都以为遇上鬼魂。
索马里先开口,他问:狗呢?
他以为我一直有条狗。我略弯腰前倾,让他看我背上的弹棉花行头。他又说:
有个手艺好,比我打零工强。
我说:这大码头,我正想找个落脚的地方。
他领我到他住的地方,也就是工棚。他住的那间,已有两人。两张床挤在一起,已无我的容身之地。
索马里指着那些刚建好的高楼说:
这些高楼,有的是房间,还没住人,你随便选一间住。你还可以用一间房弹棉花。我是包工头,可以做主。
索马里,索马里就是海盗。好像这些大楼都是他的。
他对一个小男孩说:这两天你不用上工,只去找人,要做棉被的都来。
这儿时的伙伴,真是一条好狗。
来的人不少。手艺就是饭,是衣服,是钱,也是一条好狗。白帝城,比母亲的出生地还好。要不是心里那个念头,我真可以一辈子在白帝城弹棉花。手艺就是一座城,朋友也是。
一个念头,真不是一门手艺。在日落的山冈上,与一条狗对视,我有了一个念头。一些念头,就是在对视中长出来的。说不清这念头是什么,但它不会是别的什么。它是白帝城吗?不是。也不是消失的那条狗以及往事。
索马里喝了些酒,在一边看我弹棉花。他说:兄弟,我就是你那条狗。以后,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弹棉花,吃香的喝辣的。
他还说,他师父的祖父修过皇宫,修过圆明园。英法联军的大火烧了七天七夜,还剩下石墙石柱不倒。他外婆家姓孟,孟姜女的孟,十八代以前修过万里长城。
如果是真的呢?这儿时的伙伴,让我荣耀和自豪。眼前这些高楼,是他一块砖一块砖砌的。用他砌土坎的大手,垒那么高大的楼房,像喂一头牛一样,一把草一把草地把白帝城喂得又肥又壮。
说着说着,他就抹眼泪,说这些楼房要是他的,他就让我选最好的,不用摇号。
工地上有许多狗。其实,只有一条母狗。煮饭的女工养的,母狗发情,就来了一群狗。工友们爱护这条母狗,决不让那些疯狂的公狗上它。不让母狗怀孕。白帝城完工时,杀这条母狗打牙祭。砖头,木棍,随便什么吓狗的物件,都成了这条母狗的避孕工具。这些避孕物件,也是后来的杀狗器械,一些物件的性能是通用的。
白帝城接的活儿绵绵不绝,像没完没了的扯不断的日子。我对索马里说,我要到别处去,会尽早离开。人就像河流,村庄和庄稼地,是让你经过的。
索马里说:不等几天?杀狗,吃了狗肉再走?
我说:兄弟,我不吃狗肉,饿死也不吃。
是的,哪怕吃狗能长记性,我也不吃。人活着,要有信仰。我不吃。吃狗肉,我就不算一条狗了。
索马里发动摩托,送我到白帝城的长途汽车站。他问我去哪里,帮我买票。我说自己买票,在白帝城,兄弟你帮我挣了不少工钱。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随便买张票,越远越好。有一千里就买一千里吧。怕近了,我会回白帝城,我舍不得索马里。
索马里又抹眼泪了。他刻意要消灭男人的自豪感。他给很多钱。怕我接不到活儿缺钱。又说,人到处跑,可能别处相逢,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索马里。兄弟。你真不是我亲哥哥。每次出门,哥哥给我一大包叮嘱,就是不给一毛钱。
那一票,真是万水千山。过乌江,过大渡河。我在汽车上,隔玻璃,也隔了时间,向项羽和十八勇士挥手。再过杜甫草堂,过武侯祠。四处的秋风啊,空城啊,山水啊,蜀道啊。镜照我的时间空间万物,我成为倒影。这倒影,被一秒一秒地拉长。长途是我,我就是长途。
再过都江堰。李冰在这里做官。我与他很熟,是在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路过此地,我想见他。不是见他的不朽,是求他给碗水解渴。
行程未停。过岷江,牛奶一样的江水。路过时有塌方,坠石。想象山崩地裂的灾难,无处可逃。
过雪山,草地,长江黄河分水岭。沼泽地。不知那位用缝衣针做成鱼钩的炊事班长,他在哪里给受伤的兄弟喂鱼汤?
草地。一群牦牛。一群羊。一顶灰白色的帐篷。那挂彩色红绿黄白的,不知道是不是嘛呢堆。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停留。
帐篷人家,有母女俩。再就是牦牛和羊群。不见男人。
姑娘叫卓玛。卓玛对我喊:弹棉花的,我们不要弹棉花的,只要个男人,帮我们看牦牛和羊群。
我住下来。
卓玛对我说,你不是住这里,是住在帐篷里。
我不明白。她说,帐篷不在一个地方,是到处走的。
那家的男人,卓玛的阿爸,跟地震走了。他赶马车到下边买布买糖买盐。只马和马车回来,人没再回来。我说我明白,我有一条狗,出去了再没回来。卓玛瞪了我一眼。她说:狗是你阿爸吗?
我放羊和牦牛。三五天,或一两个月,帮卓玛母女搬帐篷。从有水井的地方搬到有水井的地方。
卓玛会唱歌。那语言不懂。听得出,她是唱金瓶似的小山。好听。这歌,我上小学时就会唱,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黄狗就竖起耳朵。我会对它多唱一遍,让它知道,我是好歌手。
卓玛说,这是一首情歌。给心爱的人唱的。
我让她再唱一首,这回她是用汉语唱的:
西藏西
太阳回家的路上
格桑花开
她在等一个人
……
天冷。下雪了,我记得南方温暖的阳光。我要回到那里去。
那个晚上卓玛的阿妈做了很多好吃的,还有青稞酒。我们一边吃,一边听阿妈对我说话,我一句也没听懂。我让卓玛翻译给我听。
卓玛用汉语说:阿妈讲,她的女儿,卓玛,爱你,喜欢你。你,不要走。
卓玛钻进我的被窝,光滑的身子。
我说:会怀孕,会生孩子的。
卓玛说:女人都会怀孕,生孩子。我就是阿妈怀的孕,生的孩子。
我问卓玛:你就爱我了?
卓玛:嗯。
我说:爱有多久呢?
卓玛说:也许要等雪化了。也许一辈子。
我不再作声。爱是什么呢?也许就像一个人和一条狗,久了,再不能分开。爱可能就是对视,从眼睛深处长出的那个念头。
我喜欢一条狗,结果都是放羊。命就是这个命。
我放羊和牦牛。卓玛在歌唱:
西藏西
太阳回家的路上
格桑花开
她在等一个人
……
春天来了。雪化了。格桑花开了。
那顶灰白色的帐篷不见了。卓玛呢?
怎么来,还是怎么回去吧。
我回到南方,我母亲的出生地。
老屋场长满蒿草。黄狗见我回来,扑上来亲我。它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许它一直守在这里。
我对它唱:
西藏西
太阳回家的路上
格桑花开
她在等一个人
……
我喊卓玛——
卓玛——
哎——
卓玛是一条狗。

蔡测海,1952年出生于湘西龙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小说集《母船》《今天的太阳》《穿过死亡的黑洞》,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地方》等。《远去的伐木声》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集《刻在记忆的石壁上》《母船》《麝香》分获第一、二、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著述一千多万字,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