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王梆:钩蛇与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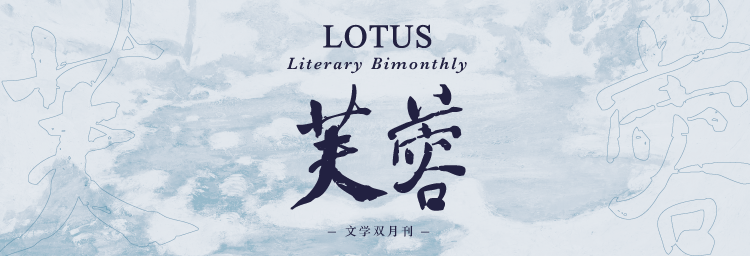

钩蛇与鹿
文/王梆
天还没有亮,阿南站在洗浴间的镜子面前,眼眶像染了一圈红墨水,头发乱得让人糟心,两条静脉曲张的腿,虚软地挨着洗漱柜,一副对称的胸骨,正从腋窝两侧缓缓伸出,孤注一掷地支撑着凹陷的胸脯。漱口的时候,阿南又毫无预兆地干咳起来,这一次感觉比上一次还要厉害,整个洗浴间都在震晃,喉咙里像涌动着一群仓鼠,却一只也咳不出来。等他咳得快死过去时,一个冥冥中有点慈悲的神,才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往他失血的肺叶里注入了一口氢气。他才总算又复活了,借着这片刻的舒展,他攒足力气,拧开水龙头,用搪瓷水杯接了半杯水,就着浑浊的灯光,一口喝掉了它。干咳似乎停止了,他扶着洗手池,试图让自己直立起来。镜子中央有一朵铁菊式的开裂,像是被谁一拳砸开的冰面,映着他那渐渐浮出的破碎的脸。
一切又变得难以忍受地安静起来,只有龙头的滴水,上了发条似的,捶打着污迹斑斑的洗手池,仍在沉睡的康复医院,感觉更静寂了。此时,病房楼外的水泥过道上,突然传来一阵窸窣的碾压声,动静挺大,却均匀沉稳,宛如身形矫捷的庞然大物,不事张扬地跨过路障。
当那个声音几乎要撞上阿南的房门时,却像被什么一口吸进去似的,突然消失了。
他屏住呼吸,拔出棉拖鞋里的光脚,走到门边,一边努力站稳脚跟,一边朝猫眼里望去。像往常一样,猫眼内一片漆黑。那是他熟悉的漆黑,每天晚上8点一过,路灯就会自动熄灭,整个病房区就会像进入宵禁一样,进入这种漆黑。他刚想转身,眼珠前方那纽扣大的黑点,仿佛被什么划亮了似的,突然变得流溢起来,有如一颗缓缓燃烧的松脂,又像一枚浸润在泪水中的眸子。他看得入了神,一时间竟忘了恐惧。
滴答,滴答,龙头的滴水声越发响亮起来。
谁在门外?发问的是安,站在阿南身后的虚空里,光着脚,脖子上挂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穿着滴水的,挂满了沉甸甸的毛球的蓝色条纹病服,湿漉漉的头发粘在额头和面颊上,手指很瘦,指甲缝里积满了黑色的淤泥。
阿南顺着安的声音转了过来。他还沉浸在那琥珀色的奇观里,一时无法辨认眼前的安是不是记忆里的安。
是信使吗?安追问,身体在声音里显得十分虚弱,像一只气囊受损的鸟,挣扎于黎明的冷空气里。
你又来了,哪有什么信使!天还没亮,再睡一会儿吧,啊?阿南后退一步,用肩膀堵住了猫眼。
打开门看看嘛!安催促着,一边不停地把湿发撸向脑后,露出鸽灰色的前额。
真的没谁,你听?阿南边说边将耳朵贴近门板,做出聆听的样子。
夫妻俩在寂静里对峙着,直到安一把扳开阿南的肩膀,拉开门,光脚跑了出去。
琥珀色的流光随着安的消失而消失了,一股阴冷的穿堂风旋即袭来,不一会儿便贴紧了阿南的皮肤。他下意识地抱住了自己的双臂,想叫住安,却喊不出来。天色在他的喉咙被卡住的当口,突然亮了。清晨的光线照着通往出口的走道,将天花板上密布的蜘蛛网照得丝丝闪光。病房楼外是一片水泥空地,很多地方已经开裂了。野草顽强地从缝隙里钻出来,刺穿腐殖,向光线充足的地方迈进。酢浆草也不顾一切开了花,两只乳白色的粉蝶,正不合时宜地绕着酢浆草那黄色的花瓣飞舞着。除此之外,整个病房区,和阿南夫妇俩刚抵达时的光景,并没有什么不同。用一个世纪前的红砖教学楼、礼堂、公共图书馆和几栋零星的教工宿舍改造而成的康复医院,内里塞满了各种数据和仪表,外表却是陈旧的,像一盘油漆斑驳的积木,散落在昔日的尘埃里。吊钟花式的路灯,攀藤绞杀的小径,一个个死去的植物园和一排排荒置的玻璃花房,更令时间仿佛回到某个泛黄的年代。病房楼里虽然住着人,却看不到任何生活迹象。一扇扇紧闭的玻璃窗,在晨光的反射下,闪着鳞白的寒光。楼道里寥寥可数的几盏声控灯泡,也几乎不超过20瓦,而且经常是坏的。阴影一年四季地包裹着楼宇之间那些本来就藏污纳垢的空间。
阿南在门边六神无主地站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回到病房里去。他掩上门,走进了空荡荡的厨房,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按下了煮水器的红键。当开水那尖厉的鸣叫声刺入他的耳膜时,他才终于感到自己清醒了过来。
厨房里的唯一装饰,是一只破旧的挂钟,可能是此前的屋主留下的,面板上的指针仍停留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阿南像其他病人那样按时执行康复计划。一种叫“日程管理”的芯片,像贴身护士一样,料理着他的住院生活。每天几点到几点,该做什么,芯片会准时向大脑发出指令。垃圾和脏衣物的收取时间是每月23日下午5点20分,领取食物和药品的时间是每周四下午3点20分,清洁队上门消杀的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到4点。
每天早上6点到7点,是室内晨运时间,设备是一台与芯片连接的仰卧踩踏机,可以全方位地调动腹肌、腰肌、臂肌和腿肌的活力。7点半到8点是早餐和洗漱时间,伴随着瓦格纳斗志高昂的音乐。随后是电磁疗时间,通常从8点一刻持续到正午12点。它其实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显得毛骨悚然,而且初始阶段还会令人感到出乎意料地放松,宛如坐进了温泉的泉眼,只是时间稍长,病人的意识就会像泥潭一样,变得浑浊起来,大脑也会陷入一种短暂而忘我的失忆状态。尽管如此,它对治疗病人出现的另一症状——某种羊角风式的肢体失控,依然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一直被列为物理治疗的首选,绝大多数患者也对此十分满意。
可安却是一个例外,从一开始,安就显露出了一副决绝的抗拒姿态:坐上电磁疗椅不到五分钟,就条件反射似的弹起来,有时还耸起肩膀,用后背撞墙,把肩胛骨的皮肉撞出片片瘀青;有时执意躺在地板上,像一颗钉子,不用胡桃钳撬开,就绝不起来。
针对像安那样的特殊状况,系统很快在芯片里加进了督促机制。只要在规定时间内离开电磁疗椅,那植入手臂的芯片,一道外表看起来完美无痕、刀片般纤巧的蓝光,就会一刻不停地冲着病人的大脑重复发出指令:“FA043号病人,请回到电磁疗椅,继续接受治疗……FA043号病人,请回到电磁疗椅……”它们就像一连串自动弹出的字符,在卡机的屏幕上,兀自跳着一种重复单调、两步一个转圈的快三。
督促机制并没有让安缓和下来,恰恰相反,她的抵触情绪更强烈了。她跑进厕所,握紧拳头,咬着下嘴唇,使出全身力气,冲着洗浴间内的镜子一拳砸了下去。在一朵铁菊的开裂中,她小心翼翼地拔出一片沾血的玻璃,瞄准手臂上方半个世纪前那个种水痘的部位,毫不犹豫地切了下去。可蓝光却丝毫没有减弱,似乎还闪得更欢快了,像一道带电的永恒的火焰。
你这样做有意思吗?你这么做和自杀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不把我也杀了……阿南半跪在地板上,搂着鲜血直流的安,一边腾出手,捡起那块玻璃,又恼怒又悲伤地递了过去。
等我们的辐射指标降到安全水平,出院了,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当务之急,是尽量配合治疗,争取尽快出院,你就听我一次,好吗?阿南又说。
安没有去接那块玻璃,一个狂风大雨的夏夜之后,它暂时回到了镜中。
为了稳住安的情绪,阿南还主动承担了烹调和洗碗的活儿。阿南是个业余的厨师,即使医院里发放的全是铝塑盒装的冷冻食品,用微波炉加热就好,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将它们排列组合,在色味上弄出一点花样来。可惜医院统一制定的硬塑盘子,清一色白底蓝边,外加配套的水杯和调羹,不管放什么进去,看起来都十分寡淡。电动煮水器那尖厉的鸣叫声,更为这种寡淡增添了一种可悲的色彩。
午饭后是健康讲座时间,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黄昏7点。讲座内容,配以清晰的字幕和画面,通过芯片,以全息影像的方式,浸入老式教工宿舍改造的病房里。画面一层层地叠加在剥落的墙漆上,像一片片透明的彩色玻璃纸,又像一层层画好的风景的皮肤。尽管看起来有点失真,久坐其中还是会出现幻觉,仿佛画里的瀑布正铺天盖地地冲刷下来。有时候,也许是数据传输障碍,声音会突然变得沙哑滞后,像一把溜达在伤口后面的迟钝的手术刀,又像二战时那种后期配声的战争宣传片。
安有时会在画面里来回穿行,像一头躁郁的野兽。有时则端坐下来,在满屏的风信子或英国玫瑰里,闭眼冥想,任由“静美”“宁神”“自愈”“自足”之类的词在眼皮上压过。坐在她身边的阿南,透过彩色的兆点,不时紧张地偷看着她。时间的老虎则蹲在天花板的缝隙里,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
晚上8点以后,是规定的睡眠时间,也只有此时,芯片才会停止工作,阿南和安才真正得以回到自己的世界。尽管如此,他俩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病房里待着。
任何外出,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都是违禁的。管理员因此还在每个楼层的拐角上装了呼吸探测警报器。无人机也不时在空中盘旋,摄下违章画面,即时上传到电子警卫处。
不允许外出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为了防止交叉辐射,二是到处都有钩蛇。钩蛇是蜈蚣和蛇杂交之后产生的变体,全然不受气候限制,自三十年前欧洲气候危机开始,就像老鼠一样广阔地繁殖,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钩蛇出没。它们大小不一,最大的,据说有象鼻那么粗。然而还是有人不断破坏规定,趁夜色逃出来,两只手大摇大摆地插入病服裤袋,在黑暗里没完没了地徜徉,虽然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转移到安全级别更高、更封闭的康复中心。
安也一样,不过比起平地和小树林,她更喜欢到天台上去,因为那里能看得远一些。每当睡不着觉,她就会悄悄爬起来,绕过阿南那露在棉被外面的光脚,拧开病房门,踮起脚,蹿上消防楼梯,卑躬屈膝地躲避着每个拐角的声控警报器,一阶阶地朝天台抵近。天台上有座红砖水塔,在无人机的摄像头里,像老式电脑中一个高高隆起的圆柱形部件,其实不过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蓄水池。病房区的建筑群里,布满了这种古老的装备,既低效,又易形成污染源,因此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淘汰了。通往塔顶的铰链扶梯却还在那里,几截踏脚的松木,风吹日晒,有的已经腐烂了。
安抬起头,在那深不可测的天穹的拱顶,无人机正定定地朝她闪耀着,仿佛在不露声色地调着光圈。尽管如此,安还是抓住了摇摇晃晃的铰链扶梯,一阶阶地爬了上去。这是一种向上的、爱莫能助的、破坏的冲动。她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冲动,她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比如五岁时偷食橱柜顶上的巧克力、十三岁时尝试初吻、十六岁以后就与父母的训诫背道而驰等,都是这种冲动的产物。
这种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她觉得体内正在生出长尾,掌上隆起的肉垫越来越坚实,步伐也变得越发矫健而沉稳起来。在她的身体下方,地面正在划开一个神秘而耀眼的裂口,源源不断地吐出那种海边才有的白色细沙和带刺的龙舌兰,太阳也露出红色的脸庞来了,那种她最喜欢的,石榴子的晶红。太阳在金色的晨衣里冥想片刻,便离开了云朵的坐骑,飘升起来,顺带把她也托上了半空。这让她感觉放松极了,像一枚在火中涅槃的箭羽,像一去不返的伊卡洛斯。反正都会死,就让我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死去吧!
每每有人违反规定私自外出,无人机就会自动上报一次。后来有人觉得病人之间互相监督协助治疗,比单纯的无人机监控更有效,于是潜藏在病患中的监督者便横空出世了。监督者将私下里窥见的,或脑海里臆想的,趁着体检,逐一填入体检单的“附注”一栏。有的监督者不仅拥有三个频道的数字电视、全息网络、平板电脑和过了一两季的电玩,还拥有除仰卧脚踏机之外的几种健身器械。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还有机会代表病方,参加管理层组织的无线会议,匿名筛选出堕落而散漫的病患,按危害程度,用鼠标将其拖入“垃圾箱”。“垃圾箱”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也没有任何(哪怕仅仅作为医用宣传品的)读物,只有重复单调的康复计划,以及基本的食品、药物和水电供给。通过讨论,他们还发展出一套家属负责制,即有人犯规(如在非指定时间外出,或在病房楼里制造事端等),家属也将一并遭到处罚。最常用的处罚方式是减少或剥夺休闲时间,断食治疗或单独隔离,等等。见不得家人受苦,病患往往会更积极、更主动地配合治疗。
然而这招对安来说并没什么用。由于安的任性,安和阿南夫妇俩已经遭到三次断食治疗了。最长一次长达一周。食品供给本来就十分贫乏,通常还不到领取时间,橱柜里就只剩半听黄豆罐头了。没有吃的,两人就只能往水里加点白糖,打发一天。阿南的体重因此急剧下降,别说踩动仰卧脚踏机,就连小便时都没把握站直。肌体的无能感,日复一日地戳刺着他的自尊心,这不能不说是安的过错。对此,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堵的。
阿南想念那个过去的安。那个常将双手搭在他的脖子上,踮起脚,对着他那冰凉的脚背,轻轻踩上去的安。现在,让我们一起跳舞吧!安会说——不管两人如何争吵,这一招总是管用的,接着阿南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沉浸在二人世界的微小确幸里。安也会顺势闭上眼睛,用均匀的喉音和微热的鼻息,哼上一首她自幼喜欢的旋律。安一直没有过远地离开童年,在她那幽深的眼帘后面,藏着一枚老邮票和一个过去的世界。那里有一块青草地,两根晒衣线和一间有些漏雨的花房。花房里有一只印花的饼干盒,里面有许多粘好的小信封,分别装着豌豆、西红柿、白菜和莴苣的种子。安想念豌豆奶黄色的花瓣,西红柿油亮的肚皮,白菜的细芽和甲壳虫大的心形叶子。她也想念她家门口的农蔬市集,一座堪称果蔬博物馆的透明建筑,钢筋和玻璃幕墙撑起的穹拱,宛如一具水晶筑起的恐龙骸骨。菜摊上全是她爱吃的时令鲜蔬,水嫩光亮,色彩斑斓。每次漫步其中,她的身体就会冒出一股食草动物的冲动,双手仿佛也变成了雀跃的前蹄。
醒醒,阿南!每当此时,安就会不顾一切地摇醒阿南,用两只兴奋的手锤击他的后背,或者用牙齿噬咬他的耳垂。等阿南好不容易醒来之后,安却消失了。安的旋律和笑声,任凭阿南如何努力,似乎也只能抓到一截微弱的尾音。
快接近晨运时间了,阿南仍握着水杯,呆呆地站在厨房里,直到芯片发出督促的蓝光,他才像冷链厂的工人那样,脱掉棉拖鞋,将自己放进仰卧踩踏机里。他全身的肌肉早已失去活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将治疗配合到底。他一边艰难地拉动踩踏机上的弹簧扶手,一边努力扳起后背,并一脚高一脚低地踩了起来。晨运结束之后是早餐时间,他殚精竭虑地估算着剩余的秒数。再做两个侧腹运动,就可以结束了……为了逃避额头上淌下的汗珠,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兆点浮动的黑暗中,他看见系着围裙的自己,正精神抖擞地站在一间明亮的厨房里。新装修的厨房,弥漫着一股榉树被锯开之后的鲜木屑味。
今天我要吃英式早餐!安坐在一张宽大的原木餐桌旁,双手像顽童一样拍打着桌面。
没问题!培根、香肠、土司、烤豆、煎蛋、炸薯条、鲜蘑菇……保证一样不少!阿南得意地应道。
然而不到5分钟,他就出来了,端着一只白色的搪瓷手术盘,上面颤动着两只白底蓝边的硬塑碗,碗里装着冒着白气的水煮麦片。
安的声音也变了,从那个清脆的安,变回了虚弱而愤懑的安。原木餐桌也回到医院食堂里那种不锈钢餐桌的样式。冷钢的幽光映着安的黑眼圈、粘满黑色淤泥的指甲,以及像裂釉一样龟裂的皮肤。(节选自《芙蓉》2021年第5期科幻小说《钩蛇与鹿》)

王梆,现居英国剑桥。作品曾发表于《花城》《天南》《山花》《芙蓉》《长江文艺》《香港文学》等杂志,入选《中华文学选刊》,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等。《单读》“英国观察系列”获《收获》2018年非虚构排行榜专家榜第六位,入围2019年青年文学奖。著有电影文集《映城志》、漫画故事《伢三》等。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