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说丨李思雨:不动的指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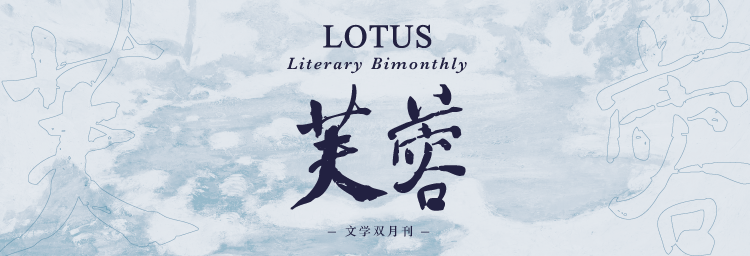

不动的指针
文/李思雨
一
周末抽空收拾阁楼旧物时,他偶然发现了这只躺在床下的旧皮箱。他都快要忘了还有这么只旧箱子。皮箱里装着他年轻时的一些物件:一把梳子,一串手链,一些信件,还有一只钟表。他记得钟表是药市寄来的,表镜在寄来时就有些开裂,不久后便脱落了。黑色的指针直剌剌地暴露着,早已不动。他捧着这只钟表,像捧着一块时间的墓碑。
儿子小虎凑上前,一把夺拿过钟表,飞快地拨动秒针,试图让它重新转动。厚厚的灰在阁楼的光影中飞舞,最后落在箱中的信封上。都是母亲和妹妹寄来的信。厚厚的一沓。他拿起一封,正好是他指责她们后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他吹开信封上的灰,光滑的指腹摸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哥哥,收到你的信后,我和妈妈觉得很伤心。这个世界上,我们只在乎你的看法,可为什么连你也要误解我们呢?你说我不上学是自甘堕落,可我不觉得这是堕落,我不需要担心未来,因为你一定会接我们去上海,到时候我可以过多少人羡慕的生活。
你只有我和妈妈了,我们有责任帮你渡过任何难关。但你曲解了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寄去的信和钱是一种罪恶的负担,说我们想绑架你,可我们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从没有想过给你增加负担,更不会绑架你。既然你不让我们寄钱,那你需要钱的时候就给我们写信好吗?
最后我们想给你寄一双棉鞋,还是以前那种料子,你说它很暖和。昨天舅舅送来两个钟表,虽然大家都在背后说不吉利,但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看就知道你会喜欢,我们也打算寄一个给你。另外妈妈和我都觉得晚一点谈女朋友好,先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突然觉得很颓丧,哀叹一声。小虎很快就对这只破钟表失去了兴致。他把钟表丢在一旁,转而玩起积木。唐远走过去捡起来,从抽屉里找出两节电池换上。钟表却像故意和他作对似的,任凭怎么拍打,秒针也只在一小格内上下跳动,不肯走动一步。他坐在地板上,对着钟表发了很久的呆,直到上身硬僵。
毕业那年国家改政策,不再分配工作,他不愿意随大溜下工厂,每天边留意工作单位边担心早晚两顿。尽管过得寒酸,但至少母亲和妹妹还能给他一点慰藉,她们每月中旬会定期寄来一封信和一些钱。这些钱让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游离于世界之外,但同时又烫手得厉害,足以烧红他黢黑的脸和脖子。以至于在得知妹妹为了多匀出一些钱寄给他竟主动退学后,他感觉自己像被丢进了火炉子。这份沉甸甸的牺牲悬在他头上,在他哄骗自己忘了那些屈辱时用力往上拉扯他的头皮,直到那些扎进脑袋的记忆又开始作痛。
在那之后他不断地做噩梦,梦里他回到了家中,母亲和妹妹早早等在门口,母女俩笑起来一模一样,眼睛眯在一起,嘴角咧得老大,露出里面的黄牙。不知道是这黄牙,还是院子里枯老的桂花树,他总闻到一股衰朽的气味。他一进门,母亲忙取下他背上的行李,踩着凳子准备放上柜顶,妹妹跑到院里的井边打水给他喝。他靠近桂花树去找那气味的来源,叶间藏着几丛稀疏的白色桂花,凑近了闻才有香味,累串的桂花像无限生发的肿瘤。这时他突然听到两声惊呼,母亲摔在地上没了呼吸,凳子滚到床底下,妹妹掉进了井里,脚上的布鞋还剩一只在井边。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经常从同一个梦中惊醒。醒来后他就再也无法睡着,坐起来颤抖着点燃一根烟,吸两口,又觉得索然无味,恐惧瞬间转换成愤怒。他把烟头摁在母亲寄来的棉鞋上,直到烫出一个灰白的洞还不解气。他愤愤地在信中控诉这一切,说她们俩自私得像魔鬼,自以为是地把变态的爱锁在他身上,并禁止她们寄信和钱过来。在那之后,他就搬到另外的地方,隐姓埋名,再没有写过信,但那个噩梦还在无边的黑夜里延续。死亡的气息总从梦里跑出来,堆满整个房间,他竟有点分不清梦和现实,甚至认为她们是真的死了。
他继续翻找箱子里的东西,里面还有三十六封信和一个拇指大的布包。那些沉甸甸的信像山一样压着他,让他无法呼吸。上大学时他身体不好,一睡觉就不停地出汗,有一次母亲来学校看他,掀开被褥就看到床板上人形大小的湿印记。母亲说这是邪祟,当下就急急忙忙缝了个布包,里面放了一块小铁板和十来粒大米,嘱咐唐远随身带着。他哪信这些,随手就把布包夹在书里,很快忘了这回事。母亲不怕鬼神,关于他的事却总要求鬼神解决。小时候有段时间他总半夜哭醒,母亲便背着他凌晨就从家里动身,走几十里山路到寺庙里去烧香。她回来后便发了场高烧,却还要感谢菩萨带回了他的魂。
他把信和钟表都收进箱子,小心翼翼地锁好。听着窗外的汽笛声,他想到了老家院墙角下的蒲公英、大雨后爬满一地的蚯蚓、一碰就落的白色桂花……他头一回感到一阵思乡的惆怅。
二
第二天,他决定带上妻儿回趟药市。突然的决定让他们都感到愕然。为什么去药市?妻子问他。他吞吞吐吐,找到一个蹩脚的理由,说是想去药市旅游。几年前突然掀起民宿热,听说药市也变得热闹起来。车窗外的田野在飞速地倒退。某个失神的瞬间,他又想起那只钟表。他看到飞速转动的指针。恍惚间竟有点分不清自己是在往前进还是后退。后来他昏昏入睡的时候,仿佛听见有人在耳边和他念叨:“唐远,现在回去还有什么意义,早干吗去了?”
“怎么想到来这里旅游?”醒来的时候,妻子问他。
他没告诉老婆孩子他们是在回家的路上,也从没有对他们提过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他害怕从妻子口中听到指责,他知道所有人听到这件事都会指责他,母亲和妹妹所做的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伟大的,他却把它们当作道德绑架的枷锁。想到这里他莫名生起一阵悲哀,他似乎永远是戴着手铐的,他的家庭、他的工作还有指责他的“所有人”,就连面对那根小小的秒针,他都无能为力。
他故作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 :“朋友推荐的。”
“好像是个新兴的乡村旅游景点,网上都说什么……”她低头翻着手机页面,“慢生活。不过这倒是其次,别像上次那个什么原生态民宿,又脏又乱……”
他又想起老家飘着奇怪气味的院子,门前那个有着白色干鸟屎印记的石墩,母亲经常坐在上面纳鞋底,身上的衣服融进了发黑的红砖墙,他痴痴地想着这一幕画面。但下一秒,那张神圣的脸庞就化为厉鬼。四周闪着幽暗的绿光,双眼凹陷在黑暗中,额顶的纹路触手般伸出,嗜血的獠牙镀上一层金色。他从想象中惊醒,后怕地抚了三下额头。
他越想越烦躁,妻子还在耳边不停数落着。他努力平静下来,闷闷地说:“你和儿子住镇上的酒店吧,我先去村里见个朋友。”
“我们不一起去玩吗?”
“我先去见个朋友,到时候给你发定位,明天你们来村里找我,再一起去。”他语气坚决。妻子再次愕然地望着他,不知所措。
他把老婆孩子安顿好,一个人踏上那条即将消失于记忆的小路。村子已经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焕然一新,把自己打扮成复古美人,和他所见过的旅游景区的村庄一个模样。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现实和记忆完全对不上。他一直对妻子照着女明星整容感到不满,现在村子也整了容,他只剩下悲哀。红黑的砖墙,青灰的瓦片,土泥沙路修成青石板路,田垄间新砌了水渠,路边新栽了银杏。他觉得自己真是来旅游的外乡人,一身名牌,和那些举着相机的人无异,匆匆走在慢悠悠的人群中。
这里慢得有些诡异,挑水做饭,喂鸡赶鹅,甚至连升起的炊烟、惊跑的黄狗都是慢的。他感觉自己变成了那根秒针,在原地徒劳地上蹿下跳。空气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味道,混合着田里尚未收割的稻穗、烧黑的泥土、黑猫玩弄过的老鼠的味道。
他向一个老伯打听家的方向,老伯一直打量着他,突然一拍大腿:“我说怎么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仔细看才发现原来是长得有点像小远,不过他比你瘦多了。”
他差点脱口而出:“我就是……”
“小远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和你差不多大。”老伯又说。
“他死了吗?”他惊讶地问。
“是啊,他一个人在上海,没有地方去,就睡在天桥下,有一天跳河自杀了,他母亲和妹妹天天在家哭啊闹啊。后来不哭了不闹了,整天说第二天要去寄钱,大家都说……”老伯突然止住,清了清嗓子,眼神看向别处,“那个,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无暇细想老伯奇怪的话,环顾四周,院子外的围墙已经拆下,换成刷得雪白的篱笆。原本有些泛白的院门漆成棕褐色,两边挂了副对联:莫笑农家浑腊酒,但将此地做自家。门上挂着“游子之家”的牌匾,右下角有“欢迎回家”的字样。他还没想好见面时要说什么,此时他希望自己可以被动地进行这个过程:她们惊喜地发现他的到来,大喊他的名字,奔过来紧紧地抱住他……
他一进院门就闻到了那衰朽的气息,和梦中的味道一模一样,他很自然地把那个梦当成了命运的预知,在看到妹妹走向水井时则更坚定这个想法。他想道完歉后应该告诉她们不要碰高处和水井,最好把这口井填了,或者把她们都接到自己家去。不,不能把她们接回去,他害怕再次承受那如铅似的爱。可她们一定会提出跟自己回去的,很久之前她们就提出要去上海团聚……他无意识地加快脚步走进院内,见母亲坐在石墩上看着天空发呆,他轻轻喊了声“妈妈”。她没有听见,依旧仰着脖子,身上穿着一件绿底碎花秋衣,这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二十年前的她。但实际上她黄褐的皮肤甚至已经融不进泥土,脸上却爬满泥土的沟壑,灰色眼珠像是随时要跳出眼眶。她一直维持那个姿势坐着,头发别在耳后,大都灰白了,像顶着满头的鸟屎。她变成了那个石墩。
一个女人从门里风似的出来,同样黄褐的皮肤,宽大的黑色衣服从头套下,一头黑发披在肩上,从背后看去就是一根黑色的柱子。她从他面前走过时浑身散发着烟味,直到看到她右手上的红色胎记,他才把眼前这个满脸疲倦的女人和他的妹妹联系起来。她径直走向水井,他喊了一声:“小芸!”
女人被吓得打了个战,转头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疑问。
她转过身来的那一刻他确认那就是小芸,她和母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坐在石墩上的母亲此时已注意到这边的情况,迅速过来上下打量这个一看就不属于这儿的人。
母女俩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但又像是透过他看向更远的地方。他有些忐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晚到二十年的重逢。他是应该道歉的,为二十年不声不响的逃离道歉,为他给她们带来的愧疚道歉,为这满院的衰朽道歉。
“这位大哥是……”女人出声打断他。
他猛地抬头看向她,她的牙齿就像他梦见的那样黄。他动了动抿紧的嘴唇,又想先给她一个拥抱再喊她的名字。
“你是来旅游的吗?”她问。
他停住所有动作,愣在原地久久回不了神,一脸惊讶地看着女人,但她波澜不惊的脸上没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又向母亲投去求救的目光,后者又继续之前抬头看天的动作,什么也没表露,平静得像村子里静止的空气。他试图从她们眼睛里找到一点恶作剧的佐证,但什么也没有。他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想起以前母亲一向忍受不了他什么也不说的,她一定会满脸担忧地看着他,在旁边急得直转,但是现在她们俩静静地站着,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缓了一会儿才接受这个结果,她们,他的母亲和妹妹,没有认出他。他变了很多,二十年光阴的加载,让他从干瘦变得肥胖。满脸的肉挤到一处,两颊上闪着油光。妻子常说他像个成了精的橄榄球,他在取笑中尴尬地转过脸去,却又故意作对似的偏不去减肥。
此时他也觉得尴尬,母亲是不喜他长胖的,这一身肉就像是故意宣战。他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出自己的身份,艰难地动了动嘴巴,嘴里一股涩味。他突然很想抽烟,便问:“这里有烟卖吗?”
“有,要什么烟?”
“随便什么都行。”他说。
小芸忙转身进了屋,他看向旁边的母亲,她扯了个笑容,问道:“要住宿吗?”
他才想起院门上的“欢迎回家”字样,原来不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他有点失落:“你们这是个旅馆?”
“是啊,院门上不是写着吗?‘游子之家’,还有那副对联,‘但将此地做自家’,是我女儿写的,写得好吧?”她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还可以写得更好。”不知怎么,他嘴边突然蹦出这么一句满是酸味的话。
“毕竟女孩子嘛,我跟你讲,我儿子读了大学嘞。”说完她发出咯咯的笑声,又好像听到了十分好笑的笑话,笑得直不起腰来。
他看着她满脸骄傲的神情,感觉眼眶有些发红,有东西要溢出,他赶紧扭转头,用力吸了口气。
“他现在在上海,上海发展好。很快他就会接我们过去一起住,大家都说我有福气呢!”母亲又说道。
话落他又开始烦躁,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吞了回去,一口痰卡在喉咙口,混杂着恶心的铁锈味。
“你的烟,二十五。”小芸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包烟,直到他从钱包里拿出钞票给她,她才把烟递到他手中。
他看着妹妹,她个子很小,眉眼却生得英气逼人,和母亲一样,嘴中说出的话都是不容拒绝的。此刻他习惯性地发起抖来,他突然害怕说出自己的身份,决定继续扮演游客的身份。
“那在我们这儿住宿咯,你看我们这院子,干净整洁,环境又好。”
他顺着她的手看向这个院子,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进院门就有种失落感,院子里的桂树已经砍了,种上一些粉色的月季。他不禁皱皱眉,指着那些月季问:“这里的桂树呢?”
“雪压倒了,”她下意识答道,又突然反应过来,“你来过这儿吗?”
“没有,”他忙回答,“但我好像梦到过这个地方。”
“那真的太巧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店名‘游子之家’,真的像回家一样吧?”母亲看看他,又看向小芸,笑得一脸开心。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他总觉得不甘心,认为这名字至少和他有些关联。
“为什么呢?我不太记得了。”母亲挠挠头看向小芸。
“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为了吸引顾客吧。”
他一脸失望,小芸看他的表情以为他是对这院子的布置不满意,忙提出先带他上楼看房间。
她领着他进了屋,他一眼就看到挂在墙上的钟,和家里的一样。只是这个保存得很好,表镜没有脱落,表盘里也没有灰,但指针却和自己的一样不动了。小芸看着停下来的他,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随口说道:“昨天换了电池,今天就不转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年,它已经老化了。”他随口答道。
“这是新的,我舅舅上个月送了两个来,我还寄了一个给哥哥。”
“上个月?”他几乎是惊呼。
“是啊。”小芸看着他一脸疑惑。
突然他又闻到那股衰朽的气味,那气味更强烈地充斥着房间,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你多久没见你哥哥了?”
“我记不清了,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她顿了顿,眼睛看向墙上的钟,又慢慢开口,“哥哥是年底出去的,我不记得现在是几月,但我知道是13号,因为我和妈妈明天要去镇上寄信。”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今天已经是26号了,所有的疑问都盘旋在脑袋里。他看向对面平静的脸,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半分开玩笑的戏谑,但她的眼睛灰蒙蒙的,什么也没有。
她又走到柜台后拿出一双棉鞋。他看着她的动作,注意到柜台上摆着的三人合照,母亲和妹妹站在他两边,两人挽着他的手,他在中间生硬地笑着。
妹妹走到他面前:“你看,这是妈妈给哥哥做的,明天我们也要寄过去。”
看到鞋面上灰白的小洞时他吓得往后退了两步,他可以肯定这是母亲寄给他的那双,可为什么现在在这儿呢?他明明记得自己给了一个流浪汉,那人四十来岁,光着脚睡在冰冷的天桥下,干瘦的身体蜷缩在纸板堆里。唐远当时就觉得他们俩很像,最后明明自己都顾不上,却趁那人睡觉时把棉鞋给了他。
“你拿它出来干什么?明天我们要寄给你哥哥的,快放回去别又忘了,本来上个月就要寄的,不知道为什么落下了,可别冷着他了。”母亲从门外走进来。
“放心吧妈妈,我一定记得,把它和信放在一起准不会忘。”
“那就好,哎,我也不记得为什么它烫了一个洞,真是可惜了,不过还可以保保暖。”
小芸忽地上前拉他:“快走吧,等会儿要吃晚饭了。”
母亲匆匆走进旁边的屋子,屋子里随即传来切菜的声音。
小芸快步走上楼梯,领着他去了房间。他还在想之前那个问题,这会儿什么也看不进,所有的东西都安静地待在原地,却在他的眼睛里快速掠过。
“可以吗?”她催促着问,似乎很着急。
“你有很要紧的事吗?你可以先去忙。”
“没有,快吃饭了。”
“你很饿吗?”
“不是,只是要省出时间来。”
“省出时间干什么?”
她摇了摇头,说突然忘了。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突然又问:“你们开旅馆多长时间了?”
“很久了。”
“你多大了?”
“我和妈妈记性都不好,我们就没记这些没有用的事。”
“那什么是有用的事?”
“给哥哥寄东西。”
他没了话,好半晌才说道:“我今晚住这儿了,晚上可以在这儿吃饭吗?”
“可以,但是要另外付钱。”
他们重又下楼,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她进去帮忙,他就坐在凳子上想着这些古怪的事情。他分不清自己在哪里,也分不清自己是在做一个无比真实的梦,还是眼下真实的生活就像梦一样。他像回到了二十年前,可母亲脸上的黑色斑块又见证了时间确是流动的。
他听见厨房里小芸压低声音对母亲说:“妈妈,他要在这儿吃饭。”
“好,那我们少吃点,饭煮少了。不过想到明天可以多寄些钱给你哥哥,我就高兴得吃不下饭。”
“我也是,但是哥哥上个月寄来的信里不是说让我们不要给他寄钱了吗?”
“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可能这阵子需要很多钱,他又不忍心让我们太辛苦,他以前从没有说过那样难听的话。”
“那我们要想办法给他寄更多的钱……妈妈,我有一个想法。我看到那个人包里有好多钱哦。”她压低了声音。他有点儿听不清,感觉应该说的是他。他努力听了一会儿,听见母亲说:“可是他醒来后发现钱不见了肯定会怀疑我们的。”妹妹说:“我们只偷一点点,我只想让哥哥高兴一点。”母亲最后似乎也同意了。偷听了她们的计划,他没有感到难过,只觉得心里一阵轻快。母女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妹妹突然抬高了声音说道:“妈妈,哥哥其实已经死了。”
“他没死!”母亲颤抖着朝她吼道。
“哥哥真的死了。”小芸开始哭,声音断断续续地飘在潮湿的空气中,“你忘了吗?张伯伯看到哥哥躺在天桥下……他没有钱,只能睡天桥下……我们去了那里,他们说早上淹死了一个人,找不到尸体,只找到哥哥的鞋子……我们还因为这个建了‘游子之家’……”
“他没有死,他没有死……”母亲拖着双脚往前走,嘴中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小芸嘴里也念念有词:“是的,哥哥没有死,明天我还要给他寄信呢。”她破涕为笑。
“嗯,还要寄鞋子。”
吃过饭,他搬了凳子坐在院里,给妻子发了位置,告诉他们明天早点来。母亲又坐在石墩上看天,妹妹则靠在栏杆上吸烟。她们都若有所思,但灰褐色的眼睛不肯流露半分情绪。已经很晚了,天还是亮的,一片淡淡的橙红色,比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更压抑。没人说话。他沉浸在记忆里,像老牛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他犹豫要不要告诉她们,这回他真的回来了。
回来又怎样呢?母亲和妹妹似乎真的不记得他了。他心里流淌着一阵悲哀,甚至有些害怕。他不知道这些年她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仿佛命运施加给他一个惩罚的玩笑。他有点后悔没有提前想好就匆忙回来,当时他只想确认梦是假的。现在,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假的。他越想越烦闷,梦里那衰朽的气味又开始缠绕在鼻尖,他逃也似的跑到楼上的房间,觉得躺下才舒服一点。
他想起给母亲准备的钱,他从钱包取出厚厚一沓钞票,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像很多年前她们给的沉甸甸的爱一样。他想不相认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他将钞票塞进信封,将信封放在枕头下,第二天她们收拾房间时一定会发现。他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三
夜里,他从噩梦中惊醒,背上渗出一身冷汗,头发像被水浸过。
梦里,他回到了药市,村里的人都来和他打招呼,他们热切地和他拥抱,抱到最后他甚至都已经失去知觉,身体无意识地前倾、伸手、揽住来人的肩膀。妹妹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她还是他白天见到的样子,狐狸似的细长眼睛,嘴唇习惯性地紧抿。他愣了一下,依旧抱住了她,两个人都只是笑,没有说话。
众人都各自回家后,妹妹领着他走了一条小路。路上,她给了他一双棉鞋,黑黢黢的,他吓得后退一步。家乡的丧葬风俗中有个程序叫“过桥”,用三条长板凳搭成桥形,上面摆一双留给死者的鞋子,法事和尚嘴里念着听不清的经词,只听见“上坡了”“下桥了”“到家了”这样的字眼。和尚说一句,就拿着鞋子走一步,偶一走神,还以为真是鬼魂自己穿上鞋子过了桥。父亲死时穿的就是母亲做的黑棉鞋。那天晚上,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睁开眼就看到父亲穿着那双鞋站在他床边看他,父亲朝他伸出手,脸上挂着无比悲痛的表情。这时,母亲喊了句“小远”,父亲忙缩回手,深深看了一眼他,一瞬间就消失了。
在妹妹的注视下,他硬着头皮穿上了那双鞋子。鞋子太小了,后脚跟露了一半在鞋外。他无奈地看着妹妹,妹妹却毫不在意地拉过他的手继续向前走。他趿拉着鞋艰难地走在泥地上,后背骤然升起一阵凉意,直觉告诉他要快点跑,但双脚却不受控制地打战。看到另一条路上的人群后,他突然有了底气,悄悄挣开妹妹的手,提出想换回自己的鞋子。
妹妹答应了,他们在一个废弃的房子前停下来,他俯身脱下鞋子,妹妹突然说:“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他抬头看向她,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放下心来,边换鞋边开口:“挺好的,挣了些钱。”又顺口提起,“你呢?过得怎么样?”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妹妹突然变了脸,冷笑一声:“我?没有工作,没有结婚,你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吗?要不是你,我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妹妹朝他逼近,他立马往后退。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他立刻回头,便看到母亲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比起这样的脸,电视里七窍流血的鬼脸甚至显得滑稽。他硬着头皮喊了一声“妈妈”,母亲没有回应。
他看到她手上提着一把斧头。他想看清楚她们要做什么,但强烈的光挡住了视线。他用力睁开眼睛,一瞬间从梦里惊醒,眼前一片漆黑,黑暗吞没了外面橙红色的天空。他越来越害怕,正准备挣扎,这时,母亲和妹妹同时朝他扑了过来……他想大叫,想呼喊住在镇上的妻子和儿子,却发现嘴巴已经被胶布封住了,挣扎着想起身,身上却提不起半点力气。
黑暗中,他感觉碎裂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李思雨,2001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现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此篇为作者处女作。

